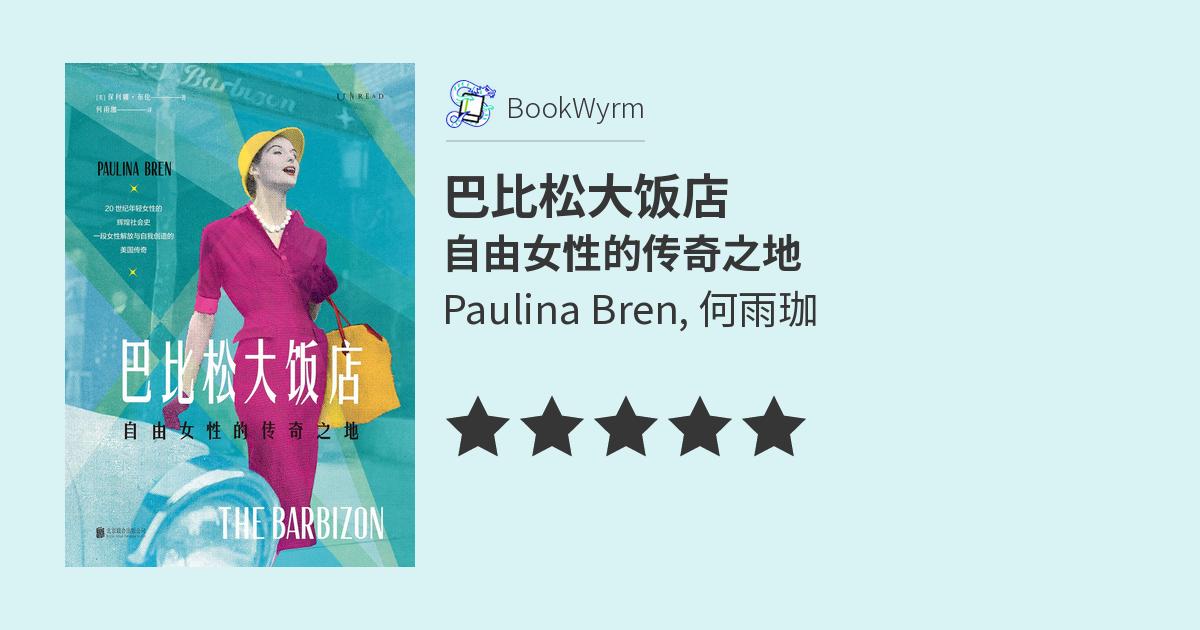"客座编辑项目是一个试炼场,即便最优秀的人在里面走上一遭,出来的时候也已然脱胎换骨。这样的环境很不一般,也很必要。主编BTB利用《少女》的版面制造继而维持了新的美国式青年主义:这片土地让你改头换面,到处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她们的梦想尚未破灭。BTB悟道可谓及时:“审视这个国家对‘青春’长久而狂热的爱恋时,我经常有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她的杂志兜售的是青春,而客座编辑们就是售货员。即便如此,《少女》为年轻女性提供的机会也称得上具有突破性。该杂志不加掩饰地为年轻女性读者提供了视觉和智识上的刺激,又为客座编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飞坪”,让一届又一届最有冲劲的年轻女性从这里起跳。这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可贵,因为在那个时代,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地位不容挑战,不容反对。男性支配,女性顺从,这完全是当时的常态。银幕上,20世纪40年代气场强大的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凯瑟琳·赫本已经让位给20世纪50年代的多丽丝·戴(Doris Day)和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正如演员克里斯·拉德(Chris Ladd)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白人男子精心设计的‘保护区’,他们以此将少数族裔拒于千里之外,也杜绝来自女性的竞争。几乎所有的高校行政人员、教授和招生负责人都是白人男性”。同样的特权实现了教育与工作的无缝衔接,不会遭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每个银行家、律师、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医生或官僚……都是白人男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BTB、她旗下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员工,同年轻的客座编辑在《少女》编辑部以及巴比松的走廊里创造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在这两个地方,女性(尽管肯定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被看到,被听到。她们是和BTB一样的主宰,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有睿智的头脑。据珍妮特·伯罗薇回忆,当时没谁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不存在,即便是在50年代的严格限制之下。"
— Paulina Bren, 何雨珈: 巴比松大饭店, pp. 278-279
#在读引用 #theBarbizon @reading@a.gup.p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