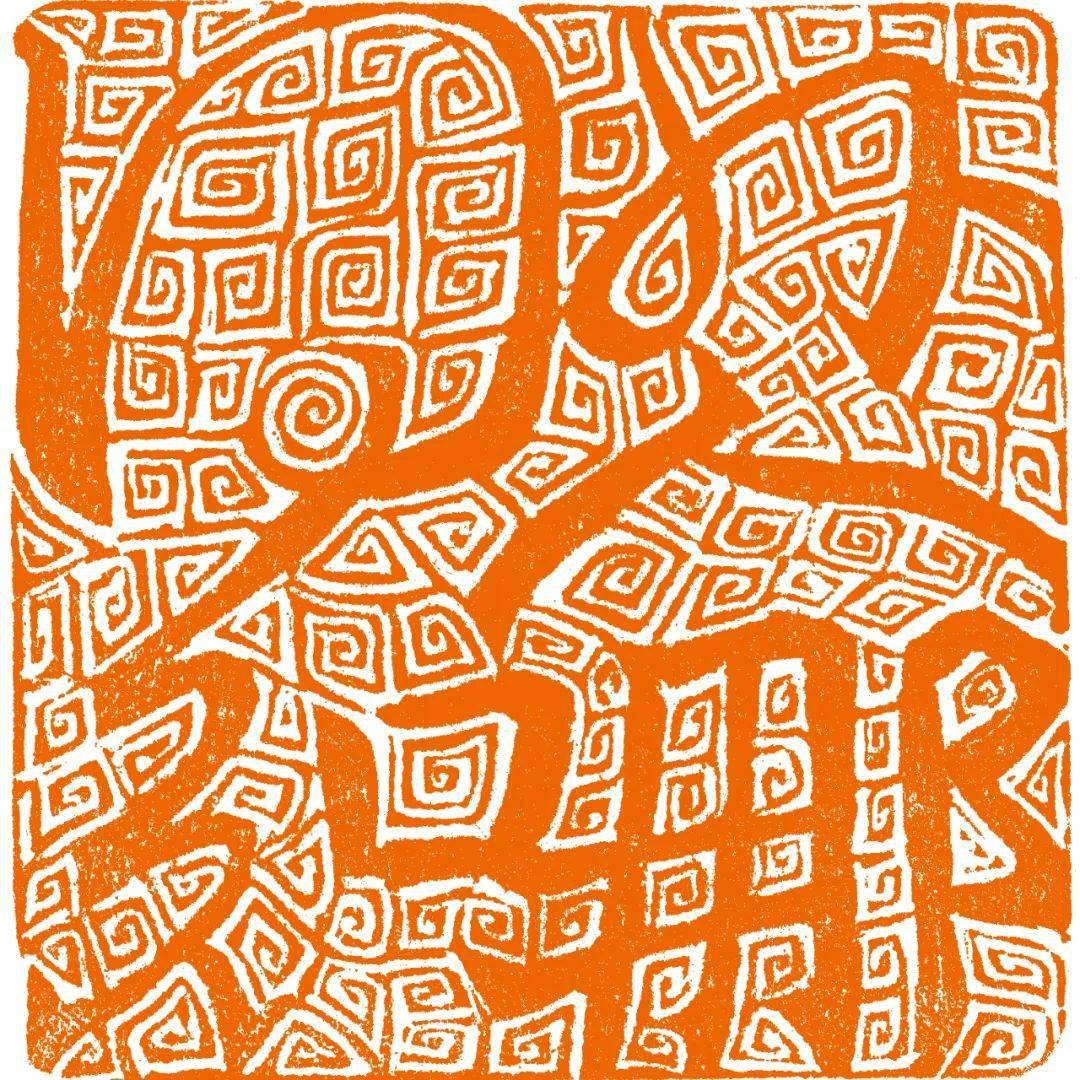本书翻译问题太多,可惜
从译者的前言来看,当是将麦卡锡译介到国内的第一人,创业维艰,值得尊敬。
但或因译本受时代局限(2002年初版),或因译者的翻译观念陈旧,总之中译本颇有不合麦卡锡原旨之处。初版之后,此书三次再版,但除了将书名从《骏马》改作《天下骏马》并微调了部分句子之外,并未大刀阔斧地改造译文。那些最致命的问题被忽略了,并未解决。近二十年过去,“边境三部曲”依然游荡在大众目光的边境,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理想国在2021年再出新版,而问题却照旧不改,不仅不改,还出现了极其难忍的排版校对错误(详见鄙人对三部曲之三《平原上的城市》的批评《 翻译与校对:旧伤不改,新错频出(平原上的城市)书评 》),可惜可叹。
最大的问题有三:一是把麦卡锡无引号的对话体改为带引号的对话体;二是把麦卡锡简洁有韵律的句子改成了冗长的句子;三是为了“照顾”读者,自以为是地改变原文结构,按自己的理解改写甚至增补不少句子,比如动不动就把“he”翻译成“约翰·格雷迪”。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独具特色的文字被改得泯然众人。随便翻开一页,试举例如下:
例1:
The waiter brought the steaks. They ate. He watched Rawlins. Rawlins looked up.
清楚明了,四个短句。主谓宾,没有更多成分。而译者翻译如下:
他们吃着侍者送上来的牛排。约翰·格雷迪一边吃一边望着罗林斯,而罗林斯也抬眼望着他。
译者将四个短句糅合成三个比较长的句子,几乎算得上是改写。前两个句子被揉成一个,主谓置换。He变成了约翰·格雷迪——这无疑抹掉了麦卡锡的风格,他老人家显然不爱指名道姓。“一边吃一边望着”则属于译者的臆想,多此一举。最后一个句子多加了宾语。原文四短句极有麦卡锡风格,而译文则丢失了这种神韵。
例2(为方便比对阅读,我将中译本对照贴在原文下面):
You ought to be happier about bein out of that place. “离开了那个鬼地方,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I was thinkin the same thing about you. “我何尝不是这么想。”
Rawlins nodded. Yeah, he said. 罗林斯点头说:“对!”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Go home. “回家。”
All right. “那好吧!”
They ate. 他们继续吃着。
You’re goin back down there, aint you? said Rawlins. “你还打算回到那个地方去,对吗?”罗林斯说。
Yeah. I guess I am. “我想是的。”
On account of the girl? “是因为你那位姑娘吗?”
Yeah. “是的。”
What about the horses? “那么那些马呢?”
The girl and the horses. “姑娘和马都叫我牵肠挂肚。”
Rawlins nodded. You think she’s lookin for you to come back? 罗林斯点点头,又说:“你认为那姑娘也在盼着你归来吗?”
I dont know. “这个我倒说不好!”
I’d say the old lady might be surprised to see you. “我认为那位老妇人见到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No she wont. She’s a smart woman. “不会的,她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
这段话发生在主人公约翰·格雷迪和好友罗林斯之间。
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直接把无引号对话改成有引号对话,泯然众人。
第二个问题,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常常自我臆想+创造。that place翻译成“鬼地方”,she’s lookin for you to come back翻译成了“那姑娘也在盼着你归来吗”。原文没有这个“也”的意思,“盼着你归来”这个表述在20年代的今天念上去正儿八经地有点奇怪——这或是上个时代的翻译腔吧?把“The girl and the horses”翻译成“姑娘和马都叫我牵肠挂肚”更是自以为是而又拙劣地如同网易云音乐的外文歌词翻译。
这样的翻译势必暴露接下来这个问题:译者丢失了原文的语言美感,把原文精心构筑的美学意义粗暴无端地直接抹杀掉了。在上引译文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忽略了“重复”之美。原文“Rawlins nodded”出现了两次,都在段首。可是在中译本中,它先被译成“罗林斯点头说”,然后变成“罗林斯点点头,又说”,效果和两个一模一样的“Rawlins nodded”所产生的重复美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再比如这两句:
Yeah. I guess I am.
On account of the girl?
Yeah.
What about the horses?
The girl and the horses.
两个“yeah”的重复,以及从the girl到The girl and the horses那种重复的美感、背后微妙的心理都在译本中完全丧失了:
“我想是的。”
“是因为你那位姑娘吗?”
“是的。”
“那么那些马呢?”
“姑娘和马都叫我牵肠挂肚。”
另外还有个毛病,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人称变动不一。这里把the old lady译作“老妇人”,但是文中其他部分遇到这位老妇人,一会儿称之“老小姐”,一会儿称为“老太太”……但其实,原文有时候只用一个词指称:she。这些问题都是译者对原文的粗暴更改。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与其他翻译相比,文学翻译有自身独特的难处。不仅要忠实传达愿意,还要传递出作者文风神韵,稍微做过一点翻译的人,也知道这个中的难度有多大。有些时候,某些文字的的确确就是“不可译”的,必须要做出割舍,否则,读上去就必然一股怪腔怪调。因而很多翻译只求不出大错,很难照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需求;再考虑普遍过低的翻译待遇,和国内不够好的翻译环境,翻译得不够传神就更是“诚可原谅之事”了。这篇短文说来说去,对译者还是不够尊敬,希望译者原谅我的求全责备,也希望读者对翻译多一分宽容。本文尽量捡那些本可避免的硬伤来谈,希望读者诸君不要误会了原初的意思。从文学的角度上说,这个译本显然是不完美的,但译者将麦卡锡引介到国内,其功不可磨灭。
再次对译者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