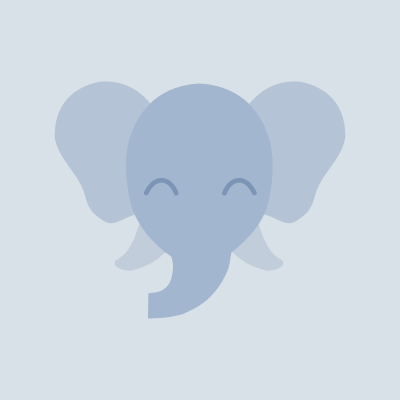少年心气——浅析《围城》中方鸿渐的悲剧人生
婚姻仿佛鸟笼,又如被围困的城堡,皆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的寥寥数语,如今已超脱本意,演化为一种普适的人生哲学。
钱锺书深谙俗世男女之悲欢离合,又有着深厚笔力,他忧世伤生写就的《围城》,仿若一幅细腻工巧的风俗画:主写婚姻,却跳脱了言情窠臼;基调悲剧,却处处有喜剧场面;成书七十年,却照样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最佳写照。人们读《围城》时,往往着眼于方鸿渐与四朵名花间的爱恨纠缠,抑或是沉醉在钱先生笔下流露的精妙讽喻,却轻视了全书主角方鸿渐的人物历程,仅仅把他当成个志大才疏、流连风月的纨绔子弟,终局的颓唐也就不以为奇。可在笔者眼中,方的一生如同浮沉于滚滚浪潮中的舢板,太仓稊米,恍若泡影,却独一无二。笔者将方鸿渐的一生分为三段,浅析他的悲剧人生,以微知著,探索《围城》的精神内核:
欧洲留学时期——“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一切的肇始,都要追溯至那个在欧洲时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方鸿渐。他留学时二十有三,已而弱冠,可照旧似少年般随心所欲,走马观花,四年换三个大学。他可以游走于伦敦、巴黎、柏林;可以从社会学转到哲学,再到中国文学;可以随意读几段叔本华和柏拉图,抒发一下感想,说些俏皮话,正如作者的总结“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兴趣”是指方鸿渐的涉猎,“心得”却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成人的处世哲学。泛览繁华的他沉醉于逍遥自在的生活中,并未意识到古老的神州大地正承受暴风骤雨的洗刷。克莱登大学薄薄的一纸文凭,不仅是遮羞布,也是流金岁月的休止符。往后余生,他在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冲突中挣扎,这段“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日子,也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月镜花。
海归时期——“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方鸿渐的“少年感”:那份漫不经心的傲气,成了他沾花惹草的杀手锏。美艳动人的鲍小姐,知书达理的苏文纨,甚至连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的唐晓芙,都曾与他打得火热。只是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白居易在《简简吟》里感叹“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般如过眼云烟的芳草美景,方鸿渐触碰过,但也只是黄粱一梦,转眼间风流云散,仍旧孑然一身。鲍小姐露水情缘,苏文纨难入法眼,唐晓芙有缘无份,佳人留不住,处境也是每况愈下,在与周家闹翻后,只得背井离乡,远渡三闾大学。
读者常腹诽钱先生不让方唐二人结婚的安排,认为他俩定会是对神仙眷侣,婚姻围城也就无从谈起。可唐晓芙亦是个满腔娇痴的豆蔻“少女”,细究两人的“少年感”,相判云泥却殊途同归。方鸿渐的心里住着个不羁的少年,渴望闲云野鹤的日子;唐晓芙则期待纯粹完美的人生。她在拒绝方鸿渐时曾言“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她希望人人都是一张白纸,可白纸终会被画笔涂抹。因此,唐晓芙不仅仅是方鸿渐的挚爱,更是另一版的方鸿渐,她有好相貌和好性情,却没有能留住这些完美特征的手段。钱锺书偏爱她,不愿将她许给方鸿渐,落入凡尘,所以她在留下惊鸿一瞥后便消失了;如果钱先生心够狠,让她和方鸿渐结为伉俪,那也只会是另一版的围城——自由的方鸿渐同样会受困于俗世囹圄,完美的唐晓芙也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摧残成珠黄色衰的模样。换言之,哪怕少了专横善妒的孙柔嘉,城堡同样也会被构筑,被围困,成为外人眼里的朱砂痣,自己心头的蚊子血。
“围城”时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三闾大学这段经历,令方鸿渐与孙柔嘉结缘,也彻底扯下了方鸿渐的浮华虚饰。赴约途中,方鸿渐不仅依赖于饱经世故的赵李顾三人,甚至还要柔弱可怜的孙柔嘉先行上桥给他壮胆。一路上的艰难险阻,皆在其他四人努力之下克服,方只是“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让别人替他跑腿”。任教之后,既无真才实学,又无深密城府的方鸿渐,在学校众人的勾心斗角与排挤倾轧中挣扎。他没有赵辛楣般壮士断腕的魄力,亦不堪忍辱自度,以求来日方长,只得黯然离去,复归上海。
《围城》至此,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故地重回的方鸿渐眼见他人荣华,自身落魄,连曾经苦恋自己的苏文纨,也在重逢时怠慢放肆,极尽刻薄之能事。留学归来时的他,可以刻意卖弄,游戏人间;转眼而立,依旧世故不通,思虑不周,人情不练达,处处碰壁、不齿于人就为势所必然。
方鸿渐的归宿——孙柔嘉,短视又敏感。可他俩确是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一对。孙柔嘉虽目光如豆,可极精明,用青涩甜美的形象俘获了方鸿渐,然后将其牢牢禁锢于自己的视野中。傲气让方鸿渐在感情上恣睢放浪,也使他化身“无赖”:愿意享受却不想负责,全心追求却无法抵抗诱惑,善于撩拨芳心却暴躁易怒。这样的跅弛形象,注定了他与三美间的爱情如流水落花,而能囚系其人的孙柔嘉,才能与之“白头相守”。
但方鸿渐依旧是个“心比天高”的少年,哪怕幽于枯井,仍然向往蓝天。他与孙柔嘉的婚姻漫溢肉身与灵魂上的矛盾,孙柔嘉的自我又加剧了这份痛苦:她讨厌赵辛楣,偏要和苏文纨一较高下,又把他牵扯进繁冗的亲族关系中,为围城添上了最后一块砖。于是,孙柔嘉囿于自保和绑住丈夫,方鸿渐囿于财产、工作、亲戚等种种矛盾,偶尔自嘲,下一刻又如阿Q般“精神胜利”,暂且忘却失意,而后复入更深层的失意中。曾被他视如敝屣的俗世,终于用他酿出的人生苦果完成了复仇。哪怕是结尾仿佛冲出了围城的方鸿渐,也不过是其人生黑夜中的点点萤火,很快就要消散不见。在笔者看来,与其把《围城》的结局当成开放性的,倒不如说是周而复始。方鸿渐从未有破釜沉舟的胆略,傲气也早被生活的琐碎淹没,所以“去重庆”不过是一时臆想,与孙柔嘉再次和好才是现实。而后两人重复吵架-和好的循环,直至生命尽头。
方鸿渐的人生悲剧——“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方鸿渐是知识分子异化出的独立个体,他既没有伤时感事的忧思,也不存救亡图存的壮志,而是怀着独有的纯真,漫无目的地奔走。这股烂漫在繁冗世俗中逐渐发展成庸懦与怯弱,方也因多次颠沛流离而失却了命运的掌握,从此彻底锢蔽于自我的理想世界。他就像单枪匹马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皆是汹涌人潮中的独行者,可又与之截然相反——堂吉诃德满身孤勇,渴求入世,方却在不断坠落的人生中一次次回首,试图寻到当初风华正茂的自己,到底一无所获。
茨威格说“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玛丽王后在上断头台的那刻顿悟曾经穷奢极欲的代价,可方鸿渐一辈子都没明白,随性的青葱岁月正是步入围城的前奏曲,当自觉被困时,如临渴掘井,为时已晚。“少年心气”给了他一个触碰倩影,阅览繁华的机会,只是“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俯仰之间,它们便如电光石火,无影无踪,无缘再见,剩下的只有身处围城,幻想彼岸的自己。尾声时的方鸿渐就似那台祖传的老钟,与时间落伍,于世间落伍,“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围城》的精神内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抗战背景下的文艺作品,或是歌颂祖国,或是悲悼牺牲,用煽情词句激起大众的爱国情。这时的钱锺书,却困于“孤岛”上海,成了危亡关头的局外人。钱先生以旁观者身份撰述的《围城》,就像炽热年代的严寒冰雪,冷峻地陈说一位风流子弟的落魄史,又以这段“无关宏旨”的小品折射出炎凉世态的荒谬,作为宏大叙事潮流下独特的一份子而流传。
世界的荒谬在于围城的林立,如同佛家描绘的无边苦海,一城放过一城拦,往复的突围也就消解了意义。方鸿渐视若珍宝的“少年心气”,那段繁花似锦的岁月,太过美好,亦成了一座充斥痴情爱欲的海市蜃楼,迷蒙了他的双眼。海归的方鸿渐,正似下了戏台、仍着戏装的小生,期冀“才子佳人戏”中的因缘际遇,却只是塞耳盗铃,掩鼻偷香,沦为荒谬俗世的牺牲品便稀松平常。
囫囵吞枣般读书的评论家,常指摘《围城》内容消极,大节有亏。然而,“慷慨高歌,从容赴死”的汪精卫,最后变身巨奸大憝;“不唱爱国调”的钱锺书,却是将一腔热血藏在冰雪文字背后。异化的方鸿渐,恰为钱先生对变革年代知识分子迷茫心态的具象归纳;他的悲剧人生,自然代表着钱老对这类人“恍惚中自欺”的鞭笞。《围城》的精神内核与方鸿渐式颓丧的悲观迥异,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式悲壮的乐观。希腊神话中遭冥府惩罚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经受无止境的折磨。在徒劳的苦役中,西西弗斯成了荒谬的代言,悲剧的象征,可他却“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以勇气战胜了天罚,变身荒谬以上的英雄。同样,在那个烽烟四起、五洲震荡的年代,依旧有无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文人志士矗立在怯懦的方鸿渐身前。灰暗的日子里,他们有的投笔从戎,有的恪尽职守,有的如钱锺书本人般身陷敌后,心系山河。这份方鸿渐不曾拥有的刚毅坚卓之精神,蹈死不顾之气节,才是真正的少年心气。宇宙的荒谬是无可辩驳的先天事实,但人类可以永怀赤子之心,如初生牛犊般奋力进取,赋意义于人生,给时光以生命,在纷纷围城中建立起自己的小天地,便可立足于悲剧之上,迎接灿烂的曙光。
罗曼·罗兰曾大声疾呼:“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虽然世界罹患痼疾,我们亦要抱病前行,如此这般,方能踏尽落花,不负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