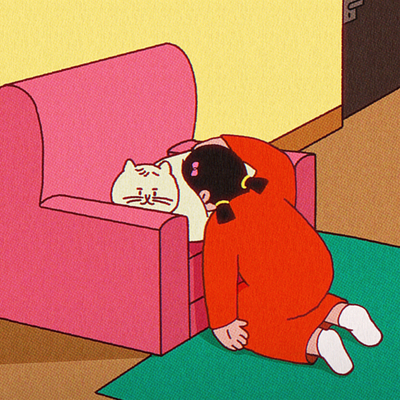实与象 ——浅谈电影《燃烧》
实与象
——浅谈电影《燃烧》
文/SILVERY
齐泽克在《变态者电影指南》中说,电影是一门终极变态的艺术。它不提供你欲求的,它告知你如何欲求。我们人类并不是天生在现实中,我们为了成为正常的人和他互相影响,生活在社会现实的空间里,很多事情要发生,比如我们都很好的装备了一套符号规则等等。这样我们在一个符合空间中的逗留就被打破了,现实分解开来。这更像是一个外物的闯入,活生生地把现实撕裂开,即表象撕裂开现实。
纵观李沧东电影,相似之处甚多,诸如残疾、边缘人物或者涉及谋杀。以此为题材,他的作品内核必然深刻且尖锐。此片虽然改自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却毫无疑问是一部超越原著以及原作者光环的作品。无需继续探讨李沧东在国际大导中的地位及成就,只需明白,他的名字虽然在大众眼中不如村上有名,但《燃烧》绝不是需要依靠原作来当卖点的作品。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继续谈论电影本身的真实。
自我,超我,本我。弗洛依德说,冲动是无声的。本我根本上是混沌的。在我们的心理能量间有个基本的不平衡间隙,被弗洛伊德成为“力比多”,这种无止境的能量,超脱了生死,也超脱了我们肉体那可怜的有限真实。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外在的能量,它在扭曲掌控我们的身体。
《燃烧》同以往李沧东电影同样多有相似之处,精神残疾的本,懦弱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已然成为一个符号。李沧东以天才般的想法直接拍出了薛定谔的猫,它跟女主角的命运互相映照——猫到底存不存在,女主角是否被“吃”掉?前一个似乎给出了答案,后一个却成为永久的悬念,而结尾处到底是存在于男主角书中的人物杀死了书中的本,还是现实中的李钟秀杀死了现实里的“本”,也已经成为了薛定谔的猫一样的存在。笔者更倾向于是前者。毕竟影片从本在家里独处做的一系列动作如戴隐形眼镜开始,视角第一次完全成为上帝视角,作为男主角的视角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无法看到本独处的场景的,而只有作为“上帝”的作家李钟秀,才能够毫无阻碍的“幻想”他笔下的人物生活状态。片尾那一场死亡,一把大火,以前文从未出出现过的“暴力”手段,终结了这个故事。
欲望是现实的一个“创伤”,电影艺术就是唤醒欲望,并且表现欲望,但是同时让它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合适地教化它,表现它。
片尾的燃烧毫无疑问是一种解放,通过燃烧这一物象解放束缚在男主角身上的一系列东西,身份阶级的差异,对于感情的复仇承载等等,书中的“我”与现实的“我”总有矛盾,因为现实的“我”是被“阉割”了的自我,或懦弱或卑微。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试图融合。当现实的“我”,在书中写下杀死本的动作之后,现实的“我”也实现了复仇和解脱的自我动机。唯一解决掉物体局部自放的途径是,成为这个物体。李钟秀在写作中,使自己成为了书中的“自我”。真实与表象在此刻的同时存在已经不能构成矛盾,甚至是解决矛盾的关键。小说与现实的界限明显,表象与现实的界限却不然。李钟秀试图确认女主角所宣称的那口井的存在,也质疑猫的存在,最终到怀疑女主角死亡是否存在,谋杀是否存在,这在电影中是虚与实的结合,让故事更加波谲云诡,如此进入到一个形而上的领域。
正如本所说:“我喜欢做饭是因为我能做出我想做的东西,还有更好的是,我能吃了它。像人类向神上供祭品那样,我为自己做好祭品后,再自己吃掉它。”如果说本的欲望是“吃”掉祭品的话,那么李钟秀的欲望也许就是由本彻底引发出来的焚烧和毁灭的欲望。平息所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人类回归死亡,或许也就不存在什么阶级差异了。跨越朝韩边界线,这边满是空虚与冷漠,那边也许会更好,也许不。但无论如何,表象毫无疑问是美的,而自我制造的表象更加迷幻瑰丽,当李钟秀脱掉所有韩国加诸于他身上的一切外衣时,他是否选择驱车跨越边界线去往他建筑的表象之国,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漂亮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