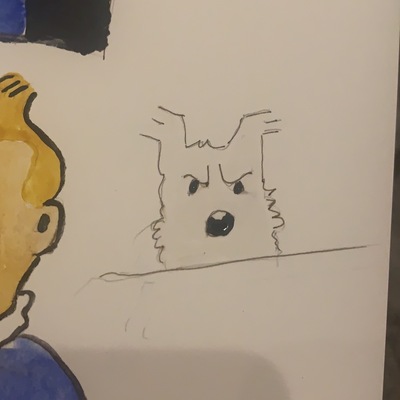主观的自留看法
看的第一本日本推理,很难想象这是80年代出版的,对虚拟现实的讨论超越时代,设定受笛卡尔的影响很深。即使是今天也不可能再从更新奇的角度翻出新花样了。作者文字功底很厉害,但感觉比起推理性,这本书的悬疑性更强。我读的是再版的台版,多加的TE确实让这部的推理性更强,圆了设定,但也打破了原本留白恰到好处的开放结局,所以对我来说有点狗尾续貂。
特别喜欢书中主角起疑心后自省的片段:
"现在的我,就像一条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一条不断吞食自己身体的大蟒蛇。吞食到最后会剩下什么?皮肤和胃囊翻转过来的自己吗?还是只剩下意识——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吃光,却依然觉得没吃够的意识?现在的我,大概 只能希望吃到最后自己还能剩下一点残渣。"
"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在结束的地方结束。这样就行。"
"我在壶里。虽然分辨不出内外,但我一直在那个壶里。"
"假如我在壶内,那么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DDST、真壁七美、姬田恒太、丰浦利也——都是真实的。我和七美在电梯里晕倒,然后我被搬入壶中。此时此刻,伊普西隆研发公司的电脑仍在不停地朝我的身体传送模拟感受。其实我眼前没有笔记本,右手也没握笔。相反,如果这是在壶外,那就意味着我已精神崩溃。我被“克莱因壶”制造的、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所纠缠,犹如一具全面失控的残骸。镜子,映出了我的身影。然而,人们为什么能断言自己在镜外、映出的影像在境内呢?谁也无法直接看见自己的眼睛。想知道自己的瞳孔颜色,就只能窥视镜子。既然如此,或许双瞳仅存在于镜中,不是吗?"
除此之外,对游戏/AR游戏的探讨也很有意思。“刺激与痛苦跟肉体上的痛苦是两码事吧?游戏需要刺激,但是否也需要痛苦呢?”莉莎在游戏世界中逐渐放飞自我,从第一次反击自卫误杀一个敌人到后来刻意屠杀了几十个敌人。她在现实化的游戏中不再抑制自己的ID,superego的影响与对ID的压制作用逐渐减弱,这是否会影响到现实中的ego呢?岗岛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莉莎在游戏中受到的痛苦给现实的她带来了严重创伤。当游戏真得做的和真实完全一致时,游戏经历对人的塑造和影响与现实经历对人的影响也大差不离了吧。
说实话,克莱因壶真得脱离概念与纸面存在于我们可接触的现实,那也应该没有壶里壶外之分了吧,就如莫乌比斯环没有正反。和蚂蚁一样,我们不会意识到任何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物,只会认为自己始终在三维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