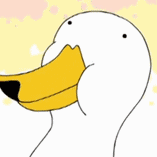理解我们自己,也就是理解时间。
亚里士多德说时间不过就是计数,就是描述事物相继发生的顺序。 牛顿说,在一无所有之处亦有时间。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一卷里讲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神在创造时间之前在做什么?”“天主正在为那些放言高论者准备地狱。”不,正确的回答是:“在天主创造时间之前,并没有什么‘之前’。” 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如果只有现在——那么现在将不再是现在,而只是永恒,这也就意味着时间并不存在。我们无法确认时间是否存在,但我们可以度量时间的流逝——不是以空间的尺度,不是以外物的标准,而只能是我们心中的感受,这就是所谓的“内时间”。 柏格森延续了奥古斯丁的思想,生命纯然是无秩序的,时间即是绵延,是不可切分的,一旦被切分就不复存在,事物一旦经过切分就不再是它们原来的面貌。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当做可衡量、可计算、可交换的(这并不是他的原创,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已经说过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要求一切都合乎比例,一切不合乎比例的都要被排除,不均匀的内时间被剔除,统一计时标准的时代开始了——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成了可以被切分以供出售的工时。 贡布里希说,时间并不存在,只有我们在衰亡。 爱因斯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看法。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随着人类观测的介入,宇宙间已不再有彻底的客观性。当我们在量子层面上观测事物,原有的时空尺度已失去意义。如果你相信大爆炸理论,你就会发现,在宇宙的远处,没有什么“现在”存在,而在未来(或者说在宇宙更荒凉的远处),时间将会流逝得越发缓慢,直至停滞——如果时间不存在了,还有未来吗?绝对的、均匀的时间并不存在,因果律并不完全可靠,宇宙间唯一真实的只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万物衰亡,唯有熵在增长,我们凭什么断定,更为混乱的那一边是未来,更有秩序的另一边是过去? 海德格尔说:时间就是从将来回到现在而来,因为我们能够确定的最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就是:我们是有限之物,是有始有终的存在,我们注定死亡。存在不过就是区分与聚合,就是时间性,就是我们的有限性。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必有一死,开始筹划自己的生存的时候,才开始本真地能在。是我们的筹划让将来来到现在。没有自由,就没有希望与未来。 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的此在是孤独的在者,每个人都只能独自筹划。我们竭力思考,想要描述宇宙完整的全貌,却忘记了,我们是从宇宙、从时间的内部进行观察,我们即是这个世界的盲点,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不再完美——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视差之见”。 究竟谁说的是对的?我们对时间有如此之多的疑问,又该怎样确认“真实”?我怎样确认“我”之外有时间,除“我”之外其他人、它物也有时间?洛维利反复告诫我们:世界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事件的集合。世界只是变化,不是存在,而是生成。世界只是事件和连接事件的关系而已。我们究竟依凭何物而在?是记忆。记忆把分散在时间中的事件联结在一起,理解我们自己,也就是理解时间。而为了理解时间,我们首先要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 尼采说:“诗是对音乐的拙劣模仿”,因为语词对情绪的表达不如音乐直观——这是我因你,因这个世界而生的情绪,这情绪真实不虚。卢卡奇说:“艺术不能是模棱两可的,但生命本身却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并不是思想透明的容器,可是书写和创作仍有意义。去思考,去记忆,去写作吧,因为这就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