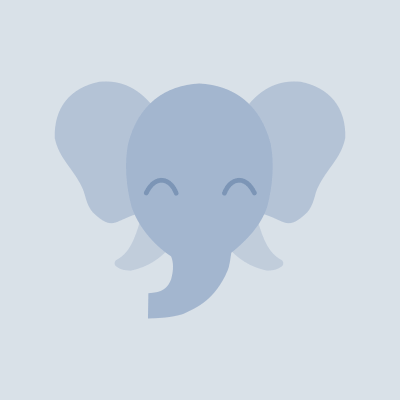#27 喋喋不休的梦
Day 27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خانه ي دوست كجاست؟
1987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从这部电影开始好像Get到阿巴斯的点了。《特写》和《樱桃的滋味》,虽然知道这些片很牛逼轰轰,探讨真实与虚构,生与死之类的哲学问题,可还是看的昏昏欲睡。
阿巴斯说:我更喜欢让观众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体贴得让你能好好打个盹,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也并无困扰。也曾有电影让我在影院里睡着了,但就是同一部片子又让我彻夜难眠,思考它直到天亮,甚至想上几个星期。这是我喜欢的电影。
我也这么想。一部好的电影就是让你睡也睡能睡的很舒服,在电影院里睡着并不丢人的,这也是电影文化的一部分。

继续讲《何处》。与《四百击》相比,同样是儿童题材,童真世界与成年世界的桎梏,体制的压抑与冲突,挣脱的力量。如果《四百击》片尾4分钟的长镜头叩响了法国新浪潮的大门,《何处》片尾的小黄花就代表了伊朗新浪潮的经典一幕。
其实我在看开头,老师在教室里训诫学生的时候影片意外退出了。重新进来不知为何已跳到影片结尾(而我并未注意到)。同样的场景,老师在检查作业,其实已是影片中第二天的剧情。直到最后老师翻开林马的作业,出现里面夹的那朵小黄花,字幕音乐一起,我才下意识检查了一下进度条。噢,原来不知怎么已经到结尾了。就好像电影院里开场还没两分钟,就已睡着,醒来已经是最后两分钟。
于是我又把进度条调回到前面,还没开始看我已经知道结尾——阿穆德帮林马的作业都给写了。当我看阿穆德为了寻找林马交还他的作业本,一波三折,上跑下跑,气喘吁吁的,我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悬念的、徒劳的无用功。而我的想法不正好就是来自成人世界的自大吗。一切以功利主义,结果为主,却遗失了我们童年时期都有过的纯真与坚持。这次打乱观看顺序的意外,真是莫大的反讽。珍爱不可避免的,拥抱偶然吧。

再说说与《四百击》。《四百击》作为新浪潮经典之作,不仅是思想上的打破现有制度,也有技术上的革新。是各种新的镜头语言和剧作技巧的出现的集大成之作。《何处》太朴素了,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包括在真实的村庄取景和非职业演员的启用。在构图上人物关系都看似平等而简单,卫西谛说“阿巴斯的镜头本身从来不主动赋予其意义,但他会让观众创造自己的感动。” 他并非有意创造客观,只是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们。我们在阿巴斯小小的电影世界里,来感悟电影,感知电影。

就像小男孩最后遇到的那个铁铺匠,他喋喋不休地讲着这家的门是我做的,那家的窗是我雕的。最后他步履缓慢地脱鞋上楼关窗然后去做工。可以想象可怜的老头孤身一人,生活中缺少着倾诉交谈的对象。阿巴斯的电影就是如此,充满着细水流长般点点滴滴生活里的感动。鸡鸣狗吠,小演员如海洋般动人的眼睛,作业本里的小黄花,这些都组成了一副田园牧歌,由童稚与真挚织成的梦。

20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