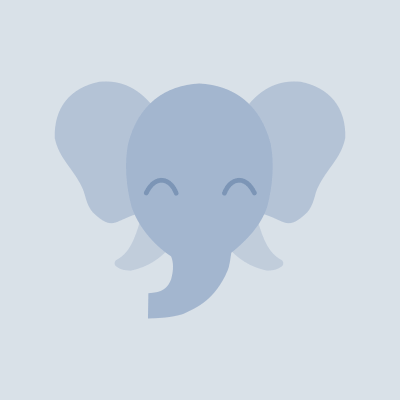#39《着魔》野蛮生长的自由运镜
Day39
着魔Possession
1981安德烈·祖拉斯基

《着魔》。我也着魔了。虽然我无数次看到过其截图和片段,第一次看完这个片子还是彻彻底底的被震到了。伊莎贝拉·阿佳妮真是惊为天人。她的悲伤,焦虑,疯狂,痛苦....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她是所有导演眼中的缪斯,她就是演员本身。阿佳妮演完这个片子居然没疯魔,可见其心理素质有多好。
居然有人说抛掉阿佳妮,这就是一个三流Cult片,绝对不是。这是我的第一部祖拉斯基,而我从未见过如此疯狂而自由的摄像机运动。电影中的运镜更像摄影师一种无意识的直觉,摄影机的运动随着人物剧情的流动而捕捉更多的能量,移动速度也在加快,越来越强烈,就像爵士中一段乐章达到高潮,亦或是着魔,摄像机也着魔了。最后戛然而止,停留在阿佳妮棕色或绿色的眼睛特写上。BOOM。烟火在夜空中爆炸了。片中所有的摄像机运动都是不合常理的。很少有“凝视”或者常规的正反打。倒是空间的旋转镜头和抖动的人物特写特别多。男主第一次进房间辞职的时候,摄像机围着桌子绕了一大圈。观众会开始想:这时是谁在看呢?这显然不是一个上帝视角,而常人的视角又不会这么迅速与夸张。男主着魔了吗?这是恶魔的视角吗?而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镜头已经快速的跳接到了下一个场景。(跳接也经常出现)而这里跳接却完全不显突兀,反而把男女主人公的焦虑表现的一览无遗。

阿佳妮被男主打后,在空旷的街道上,流着血对男主大喊“dont ever try!"时而是主观镜头、时而仰拍、时而特写时而手持。我们在一般双人对话戏中所奉承的“轴线”在祖拉斯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他要打破所有一切常规的镜头语言,破坏再重组。无论是越轴还是一百八十度的旋转镜头调换人物位置:祖拉斯基都是要让我们迷惑。不存在真正的善与恶。就像被恶魔附身的阿佳妮在耶稣圣象底下的低语呻吟。

不得不提的还有咖啡馆和地下通道的两段手持长镜头。这两段的戏剧张力就大部分来自于演员了,而摄影机(也就是我们)该做的便是冷静客观的旁观正在发生的一切:它被赋予了超越影像本身的力量。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影像不同于塔可夫斯基的诗意美丽长镜头,两者各有两者的好,他们都是视听语言的革新者。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外在能量的迸发,一个是内心深处的呼唤。
这个女人的疯狂其实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谁敢说我们内心没有创造出一个魔鬼的欲望呢?可惜我们在观看《着魔》的时候总是被阿佳妮给夺人眼球,而忽视了导演作为一部电影成功的最大要素。我们总能想到他是波兰著名禁片导演,苏菲玛索的老公,而祖拉斯基的名气,声誉与他的才华相比明显远远不匹配。可惜2016年故人已逝,我能做的就是得好好的把他的电影补来看了。
20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