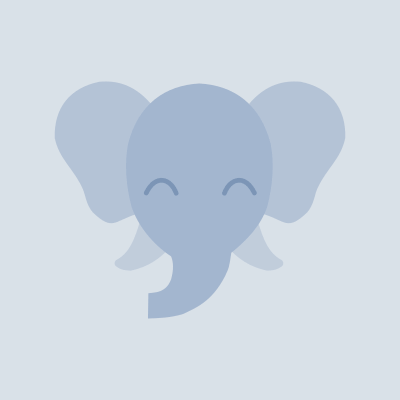对于分裂的一种理解
关于《风雨云》的所有评论,如今都落入了电影自带的分裂状态当中。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它的好,影像上的,一如既往的跳切和手持镜头。所有人也都能看出它的不好,文本上的,一个官商勾结附带家庭秘辛的狗血故事。我想要尝试提供的,是一个纯粹私人角度的,去弥合这种分裂的理解。
娄烨说这一次他想要拍摄的,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的故事。如果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当中来看,将改革开放与其他产生重大影响、乃至于成为铭刻中国文化上的集体潜意识的事件相比的话,改革开放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他表面上看上去是将选择交给人民。而如下岗这样的事件,是剥夺了人民选择的权利,从而塑造一种集体记忆。
尽管这种表面上的理解完全忽视了无形的手也是起作用的手这样一个道理,但人们已经普遍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由此而来的是,一种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你不行就是你弱或者你不努力的意识。人们自觉地接受了自己生活于丛林中的状态,而每一个人生活的道德责任,也随之由前三十年前的政府,变成了后四十年的个体。
这解释了《风雨云》中时代背景看上去为何如此稀薄。从官商的维度来讲,只要接受了个体选择,就很难以将秦昊和张颂文的所作所为追述到整个官僚体制和企业家阶层的共同个性之上。而这种追溯更难以完成的地方在于,建制派很容易将其解释为个体的选择,如既然这个世界上既有海瑞,又有张居正,那么是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决定了他们是选择清廉还是选择腐败。
同样的,也正是因为个体选择被视为决定个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当代戏剧故事的建构,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大众口中的狗血。秦昊、张颂文、宋佳、陈妍希的四角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他们在个体的通路上寻求向上流动的尝试。秦昊与张颂文构成官商体制中的一种常见同盟,陈妍希成为秦昊的白手套,宋佳游离于家暴者和稳定关系之中。如果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大部分人无异,那他们很可能就达不到影片所展现出的高度——开发区区长、上市企业创始人。反过来,而当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匹配上最后的社会地位,那必然是一种过激的,会被认定为狗血的一种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风雨云》之所以会被批评为狗血,更多是一种时代的限制。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或许去赴约,或者去见爱人,莫名被高空坠物所砸;一个人去串门,她的善良在邻里有口皆碑,遭遇类似爆炸这样的人祸,眨眼间与世界作别。这不是狗血,这是现实。
正因为整个社会都被建立于过激的个人选择之上,我们的生活就只剩下狗血和平庸两种选择,因为时代早已经退居幕后,而难以描摹。
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来自于《地久天长》。在王小帅的这部电影中,谁都能认识到,悲剧的始作俑者来自于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但在《风雨云》中,一个常规的行为逻辑链条,只能将罪恶追溯至秦昊和张颂文。
娄烨未能找到一个突破狗血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能够发掘出直击时代症候的故事模式。在这一点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参考。在描绘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的尝试时,他将整个官僚体制作为一种反抗的对象处理。如果说,《风雨云》的故事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那么可能性就存在于这里。娄烨或许能够将文本的视点从几个演员身上略作游移,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症候就可能如云一般降临世间。
娄烨可能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云的降临,更多是通过影像完成的。开场的航拍镜头,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一种全知的视角,从紫金置业大厦,转向城中村的段落,无疑是预示着资本、权力与普通人之间的压迫感。
云也可能是历史的。在开场张颂文讲宋佳送上婚车以后,镜头左移直接转接到井柏然查案。通过将不同时空并置,完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勾连。频繁的时空转换,正是试图强制将历史与当下连接在一起的尝试。
最有趣的云,是用剪辑完成的。在每一场戏的中间,娄烨运用了频繁的跳切。但在戏与戏之间,却更多采用了连续性剪辑的手法。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示,当下的经验支离破碎,而只有历史的经验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然而,这种影像上的尝试,却因为文本的缺失而显得空洞。影像赋予了文本感性的认知,而文本则赋予影像以实质的内核。《风雨云》的故事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影像的使用更多变成了一种迷离的、情绪性的呓语,而没有指代。
不过,这种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比文本本身要更切中当代人的心理状态。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魔幻的现实当中,我们的经验被分割成无数的小块。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处境,但我们却被一种无处宣泄的情绪所笼罩。
我们与《风云雨》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选择在爆发中死亡,而我们随波逐流地在沉默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