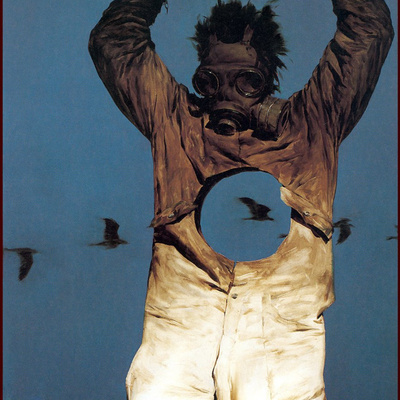情书最后一行是空白
或许情书的最后一行,就该留给空白,留给微微亮起仅能照亮你我的脸的灯光,留给满天飘飘扬扬的鹅毛大雪。
很想从理智上一五一十来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可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它实在是太柔软,永远能够以那种有力却不强烈的姿态击中我。 是回忆和情节重叠的原因吗?还是剧情本来就已经足够动人?我已经分辨不清。可谁又能拍着胸膛保证,在被风吹起的窗帘下,自己不曾对着心里的剪影动了心呢? 在评价它的时候又何必一定要把自己脱离出来,好显得自己多么客观。我乐意在回忆扎根的荒野流浪,任记忆和情节搅得一塌糊涂不分彼此,然后一心沉溺在那场吹拂不曾停歇的雪里。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青春就是有话不好好说,偏要偷偷说”。可有些话却总是开不了口,连偷偷说都做不到,藏在心里那个被打扫干净的角落。也许也曾有过开口的念头,可话滑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什么也说不出口。 我多喜欢你,却被一杯啤酒浇去了所有勇气。假装研究试卷,只想拖延时间感受你在离我不到两公尺的温热;想和你说说话,开口的第一句是询问今天数学课的内容;写无数遍的“伊藤树”,一笔一划都随着借书卡藏进图书馆里。 或许没有开口,反而让回忆的滤镜定格住了最美好的那些瞬间。于是剥离了所有的柴米油盐,只留下青春最干净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最柔和的一抹阳光总是洒在你的身上? 其实岩井俊二的《情书》不单有单人肖像的暗恋,更有黑色的葬礼、被白色埋葬的天人两隔,只不过都被他用日本式的笔触涂抹了唯美的光晕。用“释怀”给死亡画上句点,又用“呐喊”盖住了无言的眼泪。 我们曾在回忆里相拥,后来在信封流传里学会了接纳——接纳死亡,接纳不幸,最后接纳遗憾。 东方文艺作品里偏爱“含蓄”与“遗憾”,不得不说,这样的偏好太过适合拍摄青春校园片了。回看欧美那些爱情片子,大部分仍是让我感觉失了一些什么,可能就是这几分“含蓄”与“遗憾”吧。 因为含蓄,所以遗憾,因为遗憾,所以美好。傻傻偷看前方女孩背影的自己怎曾想到,“含蓄”竟在绵长的记忆延伸里,巧妙地被时光释怀,和“美好”划上了等号。 也曾忍不住去幻想,要是真能回到过去,是不是真的会拥有那些美好的结局。可世间没有时光机,也再也回不到那天。多年以后,在摇晃酒杯的酩酊大醉里,看见那个姑娘在阳光下冲着你微笑,她永远扎着马尾,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 于是想起自己也曾傻傻地鼓起勇气吐露心意。 我已经接纳遗憾了呵。 我已经接纳遗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