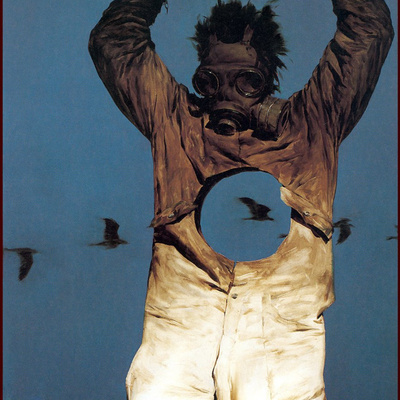最沉浸的记忆漫游
- 该文并未发布于任何评论区,豆瓣仅做记录之用,不予评分。
- 评测时游戏总时长为 2.7 小时,推荐。
- 本游戏通过 家庭共享 游玩,未发布于任何评论区。
- 文章可能持续更新,如有更新会在文末分割线标注,不会直接覆盖删减。
- 评测极其主观,但非常欢迎加我 Steam 好友,交流你对评测的想法,或者分享对游戏的体验。
游戏究竟是不是第九艺术,一直是一个未能争辩出答案的问题,不过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时,《伊迪芬奇的记忆》(后省略为《伊迪芬奇》)总是会被人拿出来——就好像,游戏这个载体,它代表着非常独特的一面。
《伊迪芬奇》并不是一款高规格的商业大作,它不过是一款小团队的作品,不过也正因如此,它也如同其他那些独立游戏一般,把游戏的商品属性抛到脑后,一心一意呈现制作人自己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伊迪芬奇》没有因此而显得粗糙,也没有因为它独立的特质,而丧失了对玩家感受的考量。相反,经过两小时的游戏后,我有一种感觉,游戏里的每一个细节,绝对都经过制作组的仔细打磨。
应该说,它在引导玩家沉浸上,做到了第一档的完美。
- 最沉浸的记忆漫游 -
有一类游戏一直被人被称为“步行模拟器”,是说游戏里主人公只能到处走来走去,做不了任何其他事情。整个游戏过程,无非就是在一个个地点之间走路,就像在模拟步行一样。 这种说法当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过它稍带贬义的态度还是让我有些不喜,因为在我看来,哪怕是步行模拟器,要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
《伊迪芬奇》就是一款步行模拟器,而且显然是彻头彻尾的那种,不仅游戏的过程只有走路,而且我们操控的角色 Edith 走路的速度极慢,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挪”。 要是放在别的游戏里,显然已经给游戏判了死刑。这样缓慢的步调,与越来越快节奏的社会相当不契合,让人不禁有些担心——难道不怕玩家玩不下去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伊迪芬奇》最高明的地方——它提供了绝佳的沉浸感,甚至让这单拿出来格外恼人的慢节奏步调,也成为了它营造沉浸感的一部分。
沉浸,是制作组在游戏里所做一切的最终目标。
从开场开始,游戏就用各种技巧把玩家拉到这个故事里来,制作组显然很清楚,讲好一个故事要比讲一个好故事更重要,让玩家沉浸入故事比故事的好坏更重要,何况故事本身也非常有味道。
游戏的开场是这样的,在短暂的Logo动画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艘客船上,打着石膏的右手拿着花束,而膝盖上摆着一本本子,翻开这个本子,我们跳接到 Edith 前往宅子的那段记忆,游戏正式开始。 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是了,这个游戏根本就没有开场菜单。无论你是在哪个进度打开,画面慢慢亮起的时候,游戏已经自动读取最近的存档,而等画面全部出现,你立马就能操控了。 这样非常反常规的方式,显然就是制作组特别留下为沉浸服务的巧思,而这样的细节在游戏里比比皆是——无论是绝对不可能忽视的,浮在场景上的绝佳字幕,还是哪怕是走在不同材质的地板上,也会有所不同的精致音效,还有很多很多,都只有一个目的——
沉浸。
所以也许你会有一个和我相似的心路历程,在害怕游戏单调玩不下去的惴惴不安中进入游戏,却一下子就沉进游戏里,被故事吸引住,一口气打通后一看,居然已经在位置上坐了两个小时。 在故事的回味之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想象过的坐在躺椅安静读书的午后,或者自己泡一壶热茶一个人慢慢细品的清晨,已经在我身上重叠。
浮动的时间,居然在这两个小时,重新属于我自己。
- 死亡与永恒的文艺 -
注意:之后的内容以剧情为主,可能涉及剧透,建议游玩后观看。
在下笔写这个剧情部分的评测篇章之前,我有想过该怎么写好这个部分——是尝试去把这个故事弄清楚?还是写写分析分析叙事神在哪呢。 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再去翻来覆去研究这个故事,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这种暧昧的虚幻现实感,只需要细细品味就好,个人自有个人的看法。
游戏的主题简单却极具冲击,女主人公 Edith 重返自己居住过的旧宅,试图找寻自己家族诅咒的真相——关于死亡。 可整部游戏玩到最后,也并没有给出所谓“真相”,而是在一段段似是而非的重放下,在朦胧中走向了故事的结尾。
死亡究竟是什么模样,是不是哀伤的离别,还是了然的释怀,又或者只是走出幽暗的地下室,把迎面而来的火车车灯当作阳光,在秋千上高高地飞起,像鸟儿一样飞向大海? 当死亡浓缩成为一场诅咒,生命的无常演变成日常,死亡是不是也无需成为一种恐惧,而只是走上王座戴上皇冠?
龟缩在旧日的大宅不是坚守传统,把死亡诅咒当作卖点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生老病死本就是世间寻常。 也许我们也不必沉溺于恐惧,更没必要困在故事中,生命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旅程,在停下来之前,只需要往前走就好。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挪威的森林》里的那句话作为结尾,那也许会是这个游戏最后的答案: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