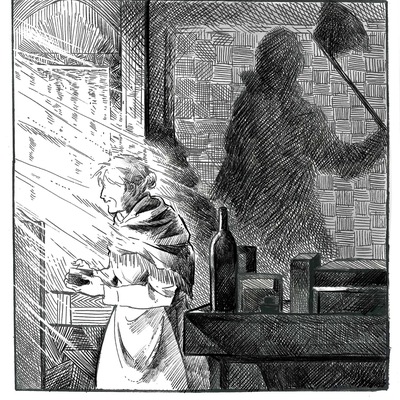《理想国》笔记
符号说明:v 观点;^ 论证;☞ 推论;ð 推导;a 结论;s 存疑;J 我的注释
第一卷
v 正义就是欠债还债。(玻,331E)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即西蒙尼得所谓的“还债”。(苏,332C)
s 受伤过的马变坏了,是马之所以为马变坏,还是狗之所以为狗变坏?(苏,335B)
J 伦理学黄金法则:道德回报的对等性。“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v 正义的人不能用他的正义使人变得不正义,好人不能用他的美德使人变坏。(苏,335D)
☞ “正义就是还债,而所谓还债就是伤害他的敌人,帮助他的朋友。”是错误的,因为“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苏,335E)
v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色,338C)遵守统治者的命令是正义。(克勒,340)
^ 强者会犯错误。(苏,340C)
^ 一个人犯错误的时候是不能称为强者的,如果名副其实,统治者是不得有错的。(色,340C—E)
^ 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苏,342D)
☞ 在任何政府里,统治者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苏,342E)
v 现实中,正义者得不到好处,不正义者将好处一扫而空。人们谴责不正义,并不是怕做不正义的事,而是怕吃不正义的亏。
☞ 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而服务的,而不正义对自己一个人有好处、有利益。
a 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色,343B—344C)
J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
^ 一般人都不愿意任公职,他们任公职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苏,346)医术产生健康,挣钱之术产生报酬……每一种技艺尽其本职,使受照管的对象得到利益。(苏,346D)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是为它本身的利益的,而是像我们已经讲过的,一切营运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做了统治者,他就要报酬,因为在治理技术范围内,他拿出自己全部能力努力工作,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治理的对象。所以要人家愿意担任这种工作,就该给报酬,或者给名,或者给利;如果他不愿意干,就给予惩罚。(苏,346E)
^ 正义是天性忠厚,天真单纯,不正义是精明的判断。(色,348D)一个正义者不会想胜过别的正义者/正义行为,但想要胜过不正义的人,却不会成功。而不正义者想要胜过所有人。(色,349B—D)
^ 有知识的人所言所行在同样的情况下彼此相似,无知识的人想要既胜过聪明人又胜过笨人;有知识的人聪明,聪明的人好,无知识的人又笨又坏。
ð 正义者跟又聪明又好的人类似,不正义者跟又笨又坏的人类似。
两个相像的人性质是一样的
a 正义的人有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苏,349D—350C)
J 类比和偷换概念
^ 世界上不讲正义的城邦,用很不正义的手段去征服别的城邦。(苏,351B)最好也就是最不正义的城邦最容易做这种事情。(色,351B)
☞ 不正义比正义强有力。
^ 不正义会是人们彼此仇恨,互相倾轧,不能一致行动。(苏,351D)不正义的人不能合作。(苏,352C)
☞ 即使是不正义的人群内部也需要有正义,否则就不能实现其不正义的目的。
J “跖之徒问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
^ 任何事物都有它独特的功能,独特的德性;功能得到发挥,是因为它的德性,功能不能得到发挥,是因为它的缺陷。(苏,353—353E)正义是心灵的德行,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苏,353E)
☞ 正义的人快乐、幸福,而快乐、幸福又是人最大的利益。不正义绝对不会比正义更有利了。(苏,354)
第二卷
v 正义的起源:人们在彼此交往过程中既尝到过干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于是大家成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把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
J 并不是所有人天生有正义的根基,倒是因为一种生存策略,才出现了法律和正义。卢梭《社会契约论》
v 正义的本质: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所谓最好,就是干了坏事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
☞ 正义是两者的折衷,大家接受正义不是因为其本身真正善,而是因为没有力量干不正义。(格,359E)
v 不正义比正义更加优越(更有利可图,祷告求情就能将恶报解除等)。(阿,362D—367E)
J 格劳孔和他的弟弟阿德曼托斯并非真正认为不正义比正义更好,但是他们始终心存疑惑,为什么在现世社会中,正义的人寸步难行,不正义的人却荣华富贵。
^ 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一个城邦比一个人大,先探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再个别人身上考察它:由大见小。(苏,368E)
^ 一个城邦的出现和发展,需要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共同努力,需要社会分工。需要农夫、瓦匠、纺织工人、鞋匠、商人、猎人、艺术家、诗人等等等等。城邦的扩大,带来资源需求的扩大,而资源又是有限的,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战争的出现需要有城邦的护卫者,城邦护卫者的品格尤为重要,需要“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且热爱智慧。(苏,369B—376C)
^ 想使城邦护卫者有这样的品性,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有益于这些品性养成的教育。(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注: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教育)(苏,376D—)
☞ 不应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苏,377E)
☞ 神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不应该将神描写成为能够变化多端,用荒唐的谎言来渎神。(苏,380D—383B)
第三卷
v 剔除恐怖以保证护卫者的勇气。(苏,386B、387B)剔除悲哀以保证护卫者的坚强。(苏,388)剔除纵情狂笑以保证护卫者的情绪稳定。(苏,388E)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保留节制的美德。(苏,380E、403)
v 一切护卫者放弃一切其他业务,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任何事情,那么久不应该参与或模仿别的任何事情。(苏,395C)不应模仿女人,因为她们“与丈夫争吵,不敬鬼神,得意忘形;一旦遭遇不幸,便悲伤憔悴,终日哭泣。”(苏,395E)不应模仿奴隶、坏人和鄙夫、铁工、其他工人、划桨人等。(苏,395E—396C)
J 歧视女性、拥护等级制度的体现
v 文体有两种,一种是叙述,一种是模仿。叙述是适合正派的人的,模仿是适合品质坏的人的。(苏,396C—397C)城邦不能同时运用两种体裁,因为“我们的人既非兼才,也非多才,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情”。(苏,397E)应剔除模仿的文体。(苏,398)
v 诗歌和曲调的形式:多利亚调或者佛里其亚调(一刚一柔)、七弦琴和短笛适合实现政治(苏,398C——399E)
J 苏格拉底的“净化”城邦,删繁就简, “很多不正直的人很快乐,正直的人很痛苦……这些话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去讲,而应该要他们去歌唱去说讲刚刚相反的话”(苏,392B);“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苏,401B),到底是节制还是清洗。
v 正确的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苏,403)
v 朴素至上: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是食品产生疾病。朴素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苏,404E)
v 健康的人才有生存价值:因为他有一种工作要做,如果做不了,他就不值得活下去。(苏,407)对于体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苏,407E)
v 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因为好人年轻时比较天真,容易受骗,心里没有坏人的原型,多年后年龄大了学习了才知道不正义是怎么回事。(苏,409B—409C)
v 心灵要爱智和激情这两者平衡,实现勇敢和温文的统一,缺乏和谐则会怯懦而粗野。(苏,409D、411)
v 统治者是年纪大一点的,被统治者是年纪小一点的;统治者必须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人。最善于护卫国家的人是护卫者中最好的,应当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也应当是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苏,412C)还要随时考察他们,看他们是否能终身保持这种护卫国家的信念。(苏,412E)
v 统治者不能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能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苏,417B)
J 苏格拉底的“铜铁当道,国家破亡”(苏,415—415D),把每一种人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是标准的社会等级理论。
第四卷
v 护卫者完全没有任何幸福,虽然城邦是他们的,但他们从城邦得不到任何好处。(阿,419)
^ 我们建立一个国家的目标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苏,420B)
J 边沁,功利主义
v 贫和富是城邦的第二害,护卫者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其进入城邦。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穷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苏,419E、422)
v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并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如我们拟议中的城邦这样规模而又“是一个”的国家,不论在希腊还是在希腊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很难找得到的而“似乎是一个”的国家比我们大许多许多倍的你也可以找得到。
v 各司其职:每个人天赋适合什么,就应该派给他什么任务。(苏,423D)
v 一个“善”的城邦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苏,427E)
v 城邦的智慧掌握在少数统治者之中: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整个其所以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与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如所知道的,只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苏,429)
v 勇敢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苏,429D)
v 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苏,430E)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及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既然一个人的较好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部分,就可以称做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城邦的节制,表现在城邦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苏,431—431D)
J 歧视女性+不平等思想+等级制:“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快乐、欲望与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身上才出现的。”(苏,431C、434B)
v 勇敢和智慧与节制的区别:勇敢与智慧分别处于国家的不同部分中而使国家成为勇敢的和智慧的。节制不是这样起作用的,它贯穿全体公民,将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起来。
v 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苏,433B),从而使得勇敢、智慧和节制在城邦中发挥作用,同时正是因为这些品质能够按照一定的职能各司其职,才有了正义。(苏,435B)
☞ 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并且数目相同。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同一智慧,让个人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苏,441C—D)
J 由大见小的论证:《腓尼基神话中的个人和城邦》
s 较大者和较小者的关系的论证
v 正义的人不允许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该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当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互相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苏,443D—444B)
v 美德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邪恶是心灵的一种疾病,丑和软弱无力。(苏,444E)美德是一种,邪恶无数,值得注意的有四种。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苏,445D)
第五卷
v “朋友之间一切共有”也可以应用到妇女儿童身上。(格,449C,“朋友之间一切共有”出自424)
v 为了同样的使用女子,我们一定要同样地用两门功课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苏,452)
^ 每个人应该做天然适合于自己的工作。(苏,453B—C)
ð 男子与女子之间天然就有很大的差别
ð 要给男子女子不同的工作,来照顾这些天然的差别。
ð 既说男女应该有相同的职业,有说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自然差别:自相矛盾。
ð 我们所说禀赋的同异,绝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只是关连到行业的同异。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假如发现男性或女性更加适宜于某一种职业,我们就可以把某一种职业分配给男性或女性。但是,假如我们发现两性之间唯一的区别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别,我们不能据此便得出结论说,男女之间应当有我们所讲那种职业的区别,我们还是深信,我们的护卫者和他们的妻子应当担任同样的职业。(苏,454E)女人男人能够有同样的才能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分别仅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而已。(苏,456)
v 女人应当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全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全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苏,457D)
^ 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和最坏的要尽少联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假如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不应该别人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中难免彼如争吵闹不团结。(苏,459E)结婚的机会对于优秀人物,应该多多益善,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地多生孩子。(苏,468C)
v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闹分裂化是恶,讲团结化是善。(苏,462B)
v 如何实现理想国:真理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国家治理得非常接近于我们所描写的那样,你便得承认,你所要求的实现已经达到。(苏,473)
☞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如今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让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哲人王”,苏,473D)
^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一样东西的爱好者,如果我们称他为这东西的爱好者说得不错的话,显然意思是指,他爱这东西的全部,不是只爱其中的一部分而不爱其他部分。(苏,474D)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只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苏,475B)
^ 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能看到每一事物本身,甚至永恒事物的人们;他们具有知识,而不是具有意见。(苏,480)
a 所以哲学家最适合当统治者。
v 真理与意见的区别: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无”、表面现象的“有”和实质意义上的“有”。它们分别对应着“无知”、“意见”和“知识”。对这三者的爱好,将人分为愚蠢的人、普通的人和哲学家。(476E-480)
第六卷
v 哲学家应该: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苏,487)
^ 现实与结论的悖论:热爱哲学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而学一点哲学并且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放下它,而是把学习它的时间拖得太长,以致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而那些被认为其中最优秀者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阿,487D)
^ 譬喻:将国家比作是一艘船,作为统治者的船长应该是精通航海术的人,可是他们却往往被窃据高位的篡权水手称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苏,488)
J 老子《道德经》: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 他说哲学家中的最优秀者对于世人没用,这话是对的;但同时也要对他说清楚,最优秀哲学家的无用其责任并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别人不用哲学家。(苏,489C)
v 哲学家天性的败坏的原因:我们所称赞的那些自然天赋,其中每一个都能败坏自己所属的那个灵魂,拉着它离开哲学;这我是指的勇敢、节制,以及我们列举过的其他这类品质。此外还有全部所谓的生活福利——美观、富裕、身强体壮,在城邦里有上层家族关系,以及与此关连的一切。(苏,491C)
^ 我们所假设的哲学家的天赋,如得到了合适的教导,必定会成长而达到完全的至善。但是,如果他象一株植物,不是在所需要的环境中被播种培养,便会长成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除非有什么神力保佑。(苏,492)
ð 何为“不是在所需要的环境”或“恶劣环境”(苏,494E):社会言过其实的职责和赞许、群众/大多数的压力和趋利主义、国家强权制度等。(苏,492C—495)
☞构成哲学家天赋的那些品质本身如果受到坏教育或坏环境的影响,便会成为某种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苏,495)
v 真正的哲学家少之又少,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象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加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便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苏,496E)
^ 一个受哲学家主宰的城邦怎样可以不腐败?
v 终身学习哲学能够得到永远的幸福。(苏,498C)
v 但是如果我们说服不了大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世,他们看到过的是一种认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苏,498E)
v 群众对哲学的恶感的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无关的地方,互相争吵,充满敌意。(苏,500B)
v 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这种哲学家也许很难避免腐败,但是总会有成功的。(苏,501—502)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苏,502C)
s 论证过程不充分,并没有解决“如何不腐败”的问题。
^ 什么是善(最大的学习)?
^ 譬喻:善=太阳,人的理智=视力,太阳的光赋予人视力,让人看见外在事物的可见本性,如同善赋予人理智,让人用理智理解外在事物。(苏,507-508E)
☞ 正如前面我们的比喻可以把光和视觉看成好像太阳而不就是太阳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把真理和知识看成好像善,但是却不能把它们看成就是善。善是更可敬得多的。(苏,509)
☞ 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苏,509B)
v 认识的四个层面/四种灵魂状态:(苏、格,509D—511E;苏,534)
意见(产生世界)
理性(实在)
第七卷
v 洞穴理论:假设一些人从小住在洞穴中,不能动弹,只能面壁而坐,一旦外界的光照过一些实物,将影子投入洞壁时,洞穴里的人只能见到影子,并且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真实。 假如解除禁锢,其中一人被迫转过身来,走动观察,一时间他会害怕失明,可终究会逐渐习惯,发现真实的事物以至于真实的光,这时他就不会停留在洞穴中的囚徒那个层次了。(苏,514—517)
☞ 洞穴=可见世界,洞穴外的景象=可知世界,火光=太阳的能力,善的理念。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便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到了善的理念的。(苏,517B—C)
ð 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苏,517D)逗留在上面不愿再下到囚徒中去,与他们共荣誉同劳苦,不论大小。(苏,519D)
ð 但是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愉快,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苏,519E)我们培养了你们……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象。须知,一经习惯,你便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苏,520C)
a 那些掌握了真正的善的理念的哲学家可以且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因为城邦培养了他们。而且他们轻视政治权利,不会以权谋私。(苏,520—521C)
J 老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v 教育不是把灵魂里没有的知识灌输给灵魂,而是发现灵魂中的能力,“使身体改变方向”,正面观看实在,观看善。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苏,518D)
v 如何教育统治者:音乐、体操:不能通向善。(格,522)手艺:有点低贱。(苏,522B)
☞ 算数: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苏,522C)学习算术的目的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而且学习算术能够提高学习其他科目的能力。(苏,525C—526B)
☞ 平面几何:几何学的对象只是永久性东西,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
☞ 立体几何:正确的做法应从第二维依次进到第三维,第三维乃是立方体和一切具有厚度的东西所拥有的。(苏,528B)
☞ 天文学:天文学是讨论运动中的立体的。(苏,528E)有一种恒常的绝对不变的比例关系存在于日和夜之间、日夜与月或月与年之间。(苏,530B)应该象研究几何学那样
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看见的事物。(苏,530C)
v 辩证法:当一个人企图依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而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了,正如我们比喻中的那个人达到可见世界的峰顶似的。(苏,532B)
☞ 对于辩证法的使用:
人群: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强与记忆,百折不挠,完整地爱智慧,关注真诚而非虚假。(苏,535B—536C)
方式:主动而非被迫地学习。
步骤:基础知识(音乐、体育、算数等)学习到二十岁 => 挑选精英将知识加以整合 => 三十岁第二次挑选,学习辩证法 => 学习辩证法五年 => 十五年左右的实际生活经验磨炼 => 五十岁:完美的城邦统治者 => 一面研究哲学,追求真理;一面处理政治事务,直到找到他的合格继承者。
第八卷
v 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的一切的方向。(苏,544E)所以先考察国家制度正的道德品质,然后在考察个人的道德品质。(苏,545B)
J 再一次的由大见小。
v 五种制度:第一种:贵族政制(理想国)。(苏,544E)第二种:荣誉政制(斯巴达和克里特),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三种: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四种: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其相反对的。第五种: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苏,544C、545C)
v 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动是因为领导阶层的不统一造成的。(苏,545D)
v 几种政制的演变:神圣的产生物有一个完善的数的周期,但有灭亡的产生物周期只是一个最小的数——一定的乘法(控制的和被控制的,包含三级四项在内,)用它通过使有相同单位的有理数相似或不相似,或减法或通过加法,得到一个最后的得数。这所有的几何数乃是这事(优生和劣生)的至关重要性因素。(苏,546)
ð 统治者的继任者素质如果越来越低,城邦也会随着走下坡路。 贵族政制的统治者由于内部素质的降低,出现不统一、不和谐,导致好大喜功、爱好战争的人占据统治者地位,贵族政制就向荣誉政制转变。 (苏,547—547C)
ð 荣誉政制的统治者好战,且爱财富;轻视文艺,重视体育而放弃音乐;好胜,自信且缺乏文化。由于缺乏掺合着音乐的例行,随年龄增长重视钱财。统治阶级运用钱财违法乱纪,钱财积累的同时对善德减少重视,进而国家重视钱财,好胜的爱荣誉的人变成了爱钱财的人,进一步转变为寡头政治。(苏547C—551B)
ð 寡头政治:政治权利在富人手里。(苏,550D)寡头政制的城邦统治者的选举有一个财产最低准入机制: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才有可能成为统治者。 (苏,551B—D)随着财富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产生了作为一个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而不事实上领导别人的的统治阶级,也产生了城市无产阶级:乞丐、小偷、盗贼等。(苏,553B——553)与此种政治制度相似的人们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崇拜金钱,省俭/吝啬和勤劳。(苏,554—554E)在贪欲的驱动下,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无耻而怯懦,而穷人崇拜财富,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统治,重新由抽签决定官职。此时产生民主制度。(苏,555—557)
ð 民主政制中,每个公民被赋予充分的自由,从而导致每个人各行其是。在这种国家里,假如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可以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
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有什么法令假如阻止你得到行政的或审判的职位,只要机缘凑巧,你也一样可以得到它们。(苏,557E)但是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向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苏,558B)与此种政治制度相似的人们的特点:沉迷快乐,朝三暮四,生活没有秩序和节制,他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并且要把它坚持到底。(苏,561D)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苏,562C)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苏,563D)这就是僭主政治所由发生的根。(苏,563E)
J 无政府主义。太平天国。
ð 极端的自由,很快产生极端的奴役。(苏,564)穷人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产生了领袖,人民领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不可抑制地要使人流血;他诬告别人,让人法庭受审;谋害人命,罪恶地舔尝同胞的血液;或判人死刑,或将人流放域外;或取消债款,或分人土地。最后,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为一个僭主,进而变成了独裁者。(苏,565D—566D)独裁者不再有内顾之忧时,他总是首先挑起一场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他假如怀疑有人思想自由,不愿服从他的统治,他便会寻找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他能看出谁最有气量,谁最勇敢,谁最为智慧,谁最富有;为了他自己的好运,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他都必须和他们为敌到底,直到把他们铲除干净为止。(苏,566E—567C)
J 《1984》,《动物农场》,文革。
第九卷
^ 僭主式人物的产生: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这些欲望在睡眠时(理性失去作用时)得到强化。(苏,571C—572B)寡头派崇尚财富,节约省俭,他的下一代由于与老于世故的人交往,欲望加强,但在傲慢无法无天与父辈教授的吝啬中间采取折中的道路,过着既不寒碜也不违法的生活,于是变为了一个民主派。而民主派的下一代则被更进一步拉近非法,从而沦为僭主——铺张浪费、纵情酒色、放荡不羁。他们挥霍自己以及父母的财产,虐待亲人,进而杀人越货,亵渎神灵。(苏,573C—574C)
v 当这些人在城邦中还只占少数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做些小恶;一旦他们成了城邦的多数,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同伙之一,一个自己心灵里有最强大暴君的人扶上僭主暴君的宝座。(苏,575C)如果人民和国家拒绝他,他就像虐待父母一样虐待自己的祖国,他们为达目的而阿谀逢迎,一生从不和任何人交朋友。由此来看,最恶的人也正是最不幸的人。(苏,576C)没有一个城邦比僭主统治的城邦是更不幸的,也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的城邦是更幸福的。(格,576E)
ð 城邦和个人性格之间都是相似的。(苏,577C)
ð 王者型人物最幸福,僭主型人物最不幸。既是幸福次序,也是美德次序。(格,580C)
v 城邦分为三个等级,每个人的心灵也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也有三种快乐,各各对应。还同样地有三种对应的欲望和统治。(苏,580D)
学习:“爱智”/“爱学”——哲学家(爱智者)
激情:“爱胜”/“爱敬”——爱胜者
欲望:“爱利”/“爱钱”——爱利者
☞ 哲学家从小就少不了要体验另外两种快乐,是唯一有知识和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人,且拥有判断所需手段和工具,因此接触事物本质的快乐是最高层次的,真实的快乐。爱胜者次之,爱利者最后。(苏,580D—583B)
v “痛苦是快乐的对立面,所以脱离了痛苦就是真正的快乐,没有了快乐就是真正的痛苦。”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存在一个既不快乐也不痛苦的心灵的平静,是两者的中间状态。(苏,584—584C)没有经验过真实的人,他们对快乐、痛苦及这两者之中间状态的看法应该是不正确的。(苏,584E)
ð 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心灵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苏,585D)只有心灵以及关于心灵的知识,才有可能接触到永恒的真实和实质。
ð 王者的幸福远远超过了僭主的幸福。僭主暴君离真正固有的快乐最远,王者离它最近。(苏,587B)
s 586E没看懂
v “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的人是有利的”是错误的。
^ 塑造一个三头怪兽比喻为人,人拥有不同性格,应当照顾好不同性格使各个部分和谐相处,从而促进他们生长。(苏,589E)
☞ 奴隶天生应该受到神圣的指挥者的统治,这样对于大家都是比较善的。(苏,590D)
☞ 我们管教儿童,直到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确立了所谓的宪法管理时,才放它们自由。(苏,591)一开始的管理,一开始的不自由,是为了将来的自由。
☞ 不正义者如果做了坏事没有被处罚,他的兽性部分就没有得到平服和驯化,会让他变得更坏,从而更加远离自由和幸福。(苏,591B)
第十卷
v 诗人(例如荷马)崇尚模仿,但是他们模仿的却并非事物的本质(理念),他们模仿的是影像,是理念外化的具体事物。自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苏,600E)所以,诗人不是真正懂得,他们不能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本身只是提供解决方法的人的模仿者。
v 事物有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任何事物的使用者是对他最有经验的,掌握着真正的知识;制造者则是遵从使用者的教导来获得正确的信念;至于模仿者(诗人、画家等)对于自己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所以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苏,601D—602B)模仿只能得到“大概”,这是远离理性的要求的。 (苏,603C)
☞ 应该将模仿者驱逐出城邦:他们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会腐蚀最优秀的人物,使人变得情绪化,从而远离理性。(苏,605B—C)
v 灵魂是不朽不灭的。(苏,608D)“不正义、无节制、懦弱、无知”这些因素都会使心灵变恶,但是它们不能毁灭心灵。
s 关于灵魂不朽,参考柏拉图《裴多篇》
v 灵魂的本质就在于爱知,正义本身就是最得益于灵魂自身的。 (苏,611E)正义者终将获得正义的报酬,不正义者终将得到不正义的惩罚。(苏,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