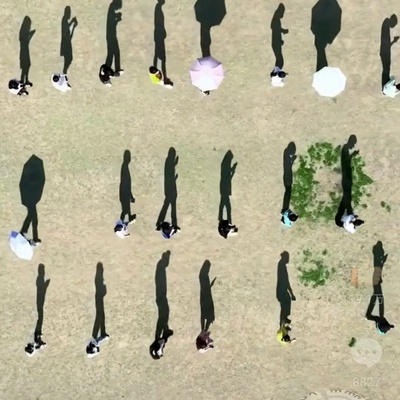文化批评 |我们为何没有动漫批评?——以 《灵笼 incarnation》 为例
近年来,国漫崛起的呼声此即彼伏,以至于网络上经常有人吐糟国漫“又崛起了。”这样的吐槽看似令人无奈,实则是对隐藏在铺天盖地的国产动画电影民族主义宣传的一种反感。笔者也认为,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是由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本族成员来进行书写,而应当单纯评价其作品本身的价值。此外,倘若我们以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视角来评判,“作者之死”的号角早已吹响,那么作品的价值更多的被放置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再生产关系。因此,我在本篇文章当中想要提出一个论点,那就是当我们在观看动漫的时候,合格的动漫批评应当出现。但是倘若读者的姿势水平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大家不会被情怀感动,另一方面也能够给这个行业有一个正向的回馈机制,而更重要的是,读者们应当有一个渠道来获取如何来阅读一部动漫的思想性维度或曰动漫批评。
作为一个资深的动漫迷来说,笔者大约是从初中时候开始入的坑,如今已经研究生即将毕业。由于,笔者本身从事文化批评,同时也阅读过大量的哲学著作与文学理论,故如今再来回顾某些经典动漫时候,往往能够发现很多背后的深层次叙事结构以及符号隐喻。
我想argue的是,在我们普遍无脑的动漫市场当中,不论作者与读者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领域的时候,即便有些许好的作品的出现,同样也少有人懂得欣赏和阅读其中的奥妙之处,因此也就无法促进这个产业的良心发展。实际上动漫领域也仅仅是我们文化领域的一个小小的样板,我国整体上的文化产业较为原始,不论是图书出品,电影批评,以及艺术策展等方面,均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剩余价值》播客曾经做过一期关于游戏研究的节目,其中道出了我国游戏文化的艰辛发展,以及非常腐朽的游戏观霸权。在此,我国的动漫和游戏基本上出去相同的处境当中,不知何时我们在可以从这种“游戏成瘾论”“动漫低龄论”当中走出。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国的电影批评领域日渐成熟,倘若要号召一种动漫批评的形成,我们大可以先以电影批评,文学批评,戏剧批评,文化批评等角度入手,最终形成一种以动漫为批评主体的批评领域。换言之,由于目前我们尚未出现一种严格的动漫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先以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来围绕动漫作品这一批评对象来进行研究,故此可以给动漫读者提供一些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动漫的理论框架。
此外,大多数具有一定理论程度的读者对于国产动漫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因此也缺乏了一种自发性动漫批评的动力。对于动漫场域当中日漫的受众来说,观众自发的一种批评行为会更加广泛的多。例如,这种不知所云的批评(图1)和一种合理的批评(图2)。也许是因为日漫的观众受众面更多,而国漫很有可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当我看到个人比较欣赏的优秀动漫作品并没有相应的严格的批评的时候还是会略显悲伤。
本文的后半部分尝试以今年新出的动漫作品《灵笼 incarnation》为主体来进行一种动漫批评。
这部动漫作品在我心目当中虽然说不上像《攻壳机动队》《心灵测量师》《秦时明月》这类动漫作品具有经典地位,但笔者依然认为这部动漫开启了一种国产动漫领域的思想类动漫实验。换言之,就是某部动漫作品具有一种很具体的讨论主题并且这种主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的时候,我姑且将其称之为思想性动漫。比如,《攻壳机动队》和《心理测量师》均在后人类主义(post humanism)语境下探讨了前者探讨了“什么是人/灵魂?”;后者探讨了一种“极端的监控社会下人的境况”的问题。
而《灵笼 incarnation》这部作品恰恰是把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即“什么是活着?”放到了一种近未来赛博朋克的极端条件下来进行讨论,并且加入了很多非常具有试验性的设定,从而以一种布莱希特“陌生化”的戏剧理论效果来达到让读者反思现实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创作手法在西方动漫和科幻作品当中被广泛应用,起到了一种在分析哲学上“思想实验”的效果。
这部作品的世界观设定在一个近未来的世界当中,在这里由于刚刚经历过一场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人类已经无法在地球表面进行生活,从而使得仅存的一小部分人类登上了一个名叫做“灯塔”的大型封闭建筑当中。在这里,一切目标以繁殖人类为主要目的,从而伴随着“灯塔三大生存法则”(1.摒弃旧世界的所有亲密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亲情、爱情;2.按照基因将居民划分为尘民和上民,物资按贡献点分配,年长者远行;3.无论任何人都要以光影之主为信仰)颁布之后,曾经“旧世界”的各种伦理关系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生产关系。
我在本文当中先以一种隐喻解读的批评方式来谈论我认为这部作品的优秀之处,在之后的文章当中(应该是这一季结束)我会尝试来回答这部作品提出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活着?”(由于目前这部动漫只播出了7集,笔者目前的解读都是基于前7集的一种解读。也许最终解读会与整部作品的最终立意有所冲突,但至少是符合我对与前7集的理解。)
首先我们从这部作品的名字谈起,这部作品的名字以一个汉语词汇“灵笼”和英文词汇“incarnation”两者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整部作品的完整名字。这个名字一定程度上也致敬了《攻壳机动队》 (Ghost in the Shell)。.两者相互关联却又有些许的符号学意义上的区分,因为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解,不同的言语(speech)只能在其相对应的语言(langue)当中来进行理解或产生意义。
先谈论一下这两个词语的一阶含义(first-order),我们可以把灵笼和incarnation看作是两个相同的意思,至少字面上来说这部作品是这么展现出来的,“灵笼”顾名思义是指灵魂的笼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生命观即“灵魂被困于肉身当中”;“incarnation”也有化身,道成肉身之意。这个一阶含义紧密的连接了作品当中“光影教”这个宗教的隐喻,且两者都来源于柏拉图。在柏拉图的《斐多篇》当中,柏拉图详细的论证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柏拉图认为灵魂与肉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只不过灵魂是暂时被困居在肉体当中;其次,灵魂的目的是去追求真理获得知识,而肉体总是在干扰阻碍灵魂的求知过程;最后,通过对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从而达到了柏拉图的目标,即灵魂是可以求得真知的。这种观点恰好能够结实这部作品“灵笼”的隐喻。
其次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语具有怎样的二阶含义,“灵笼 incarnation”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韦伯的著名概念“铁笼 iron cage,”两者不但在中文当中还是英文上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根据豆瓣网友Nosce te ipsum在其文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铁笼“Iron cage”文本解读”当中对于“铁笼”的五层解读具有借鉴意义:
1.社会理性化的困惑。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哈贝马斯“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概念相似,理性化也成为了韦伯社会观的重要名词。日常生活、工作的精确化,计算化,复式簿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被剥夺了情感,“宗教伦理式的救赎和皈依”,成为了一种“不自得性”、“无根漂浮”的无力呼喊。日益成长着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人不仅脱离了歌德笔下纯粹的浮士德式的生活,成为了“为了赚钱而赚钱”的机器工具,就像《摩登时代》工业生产下,“无意识”人们镶嵌在机器里无奈的“惨白和叹息”。理性化下社会物质财富急剧膨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文明的快速现代化,而同样时代下的单个个体的价值和品格的丢失是否就是必须承受的现实?
2.财富物质的功利化。韦伯在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时,把财富的创造作为重要的链接点。天职下的职业劳动,使得财富被巨额地创造。意料之外的是,物质财富有很强的占有性,侵蚀性,创造者在寻求中难以保持“单纯的自我坚持”,由是造成一种世俗式的引诱。“它从一件教徒随时可以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不可撼动的铁笼”。财富由自我救赎的附属品变成了目的。从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看,个人在财富享有中“”而丧失了应有的经济德性,主体自身的“虚空”瓦解了原有的价值伦理,个人完全被物质化。
3.法权力下的个人“湮没”。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很大一部分成就便是对经济理性下组织结构,国家统治类型的分析。经济组织中科层制的理性规训,使得效率,去复杂化成为了企业追求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权力结构的“优置化”才能使企业系统的“计算性和精确程度”达到最高水平。而理想类型分析下的法理型国家,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在了理性建构下最完美、完善的法律秩序之下。这种机构秩序,个人被强化,称为权力的“湮没”品。精英统治并不能使个人的完全理性过渡到整个组织、社会、国家的“完全合理性”,纳粹主义的诞生便证明了这一点。个人权力的出让,并不能成就集体的完全德性。(完全追崇理性的日耳曼民族为何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理性的作祟?固有的文化传统?)
4.碎片化——哲学的自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下,由于主题自身权力的“让位转移”,单个个体自身在社会视域中无法获得“自我诉求”而被分割,“孤立”,由是自我的实现在现实中便呈现为对财富和权力“依附”状。碎片化的个人生存形式难以获得主体的寻求。而“转移”后的主体联系,恰恰催生了集体性的主体主义,它在寻求独立存在的完整性时,又试图寻求和他者的内在关联,即自身或自我,与真实的他者、对象二者的边缘状态。换言之,日益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西方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都是理性主体对他者的侵蚀,将他者变成“自我”。应该说文化的侵蚀更具怖感。现代语境下,汉语生活日渐布满了外来文化的文字话语,社会生活的麦当劳化,语言,文字,交际,服装,艺术,美,知识。。。都披上各式的外衣。日常生活的言语诠释也镶嵌着不同文化内容的“指向性”。文化无优劣之分,文化之间的侵蚀是否存在可能?
因此,笔者认为,从“铁笼”这个二阶隐喻的解读来看,本部作品实际上是想让读者来反思自身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是“灵笼”?“铁笼”?还是“积极自由”的活着?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光影教”的这个宗教设定,在这部作品当中光影教的这个隐喻和其所作所为简直是具有一种十分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启蒙批判,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出发来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当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光影教的基本隐喻为“光”和“影”,同时动漫作品当中还不加引用的使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即我们都是一群生活在洞穴当中,手脚戒备锁链捆绑之人,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是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而那影子也不过是洞穴当中微弱烛光的投影,唯有那个能够挣脱锁链并且走出洞外之人才能获得理念之光的照明,从而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柏拉图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被后来的基督教融合吸收,从而出现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局面。在此之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出现,同样以光的隐喻为名,意味着为世界带来光明,祛除黑暗当中的矇昧,同样地,笛卡尔也有自然之光(natural light)的表达。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广泛反思为何启蒙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子弹的出现。《启蒙辩证法》恰恰就是对于这种现象的充分回击,即启蒙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启蒙丧失了自己的批判性,从而成为了权力,对人进行统治。而动漫当中的“光影教”恰恰就是用启蒙之光当作一种刑罚工具来对人加以“净化”。这种荒谬性,恰恰正是我们在西方哲学当中看到的,工具理性对人的暴政。
在作品当中,这个“光影教”恰恰就是用的一套启蒙话语来对民众洗脑,实际上就连统治者自身都根本不相信。而我们发现最终能够走出洞穴寻找真的过程叫做“远行,”就是把老年人流放到地面而已。
在隐喻层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就是“灯塔”的监狱原型设定,这个隐喻毫不意外的来自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当中所借用边沁“圆形监狱”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全景敞视主义”(这点在我上一篇文章当中有详细的介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专门来谈论了规训社会当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是如何通过全景敞视这样一种隐喻模型来进行运行的。实际上,福柯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即微观权力。这样的微观权力弥散在整个规训社会当中,主要通过对于主体(subject)持续不断的凝视从而达到使主体将规训内化,换言之,自我审查。这样,主体就可以在规训社会当中被重构(reconstruct),成为这个社会所希望生产(produce)的人。在这部作品当中,如此这般的审查和自我审查通过法律,权力,宗教,生命政治等多个维度对个体进行重构,最终大多数的人不论是上民还是尘民都对自己的处境习以为常。
在此,笔者仅仅是简单讨论了文章当中非常明显的三大隐喻,其余还有非常多的细节和设定有待挖掘,希望我能够在后面的文章当中进行更加完善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