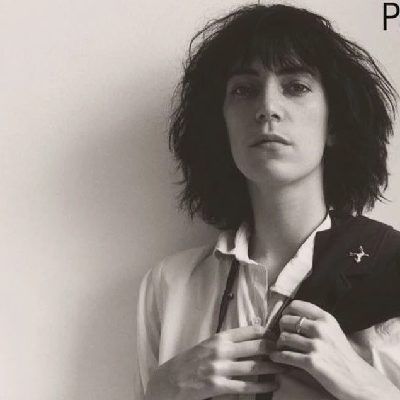用雪花写作的人
在由两个人的沉默所搭建的桥梁上,罗伯特·瓦尔泽以那张像被闪电击中过的又似孩子般的圆脸与卡尔·泽利希开启了二十年的友谊。在瓦尔泽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也许只有这一位朋友。他们在各种天气里散步,并且谈话,谈论文学所包含的一切。
瓦尔泽那些结晶一般的句子,有时候不只是在隐喻层面有效,在现实层面也被他实现:“人不能总是在阳光下行走。”有时候雨很大,而他们没有带伞,两个人就淋着雨,继续用双脚走得尽可能得远,有人邀请瓦尔泽上车他也会拒绝。瓦尔泽是固执的,即使累了但只要还没到达目的地就不愿意休息,在疲乏的时候也不愿意泽利希搀扶他。人必须得走他自己的路,对瓦尔泽来说,人生之路与脚下的路都必须自己走完。
“为了追求个人趣味,我让自己偏离常轨太远。”也许“固执”是可以形容瓦尔泽的一个词,不过固执只是他个人选择的表现。他选择了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作家圈子保持一定距离。他几乎不会抗拒成为一个流浪者的倾向,“流浪者”这个词语曾多次出现在他们的散步谈话中。就像这种倾向所传递出的,瓦尔泽也不喜欢有负担,他不喜欢太新的东西。泽利希带他去买新衣服,他却想要买一些能让他穿得土气的衣服。他的牙齿严重损坏了,但他不愿意去修补。
如同瓦尔泽对待物、对待时代和社会所表现的那样,对人他也拒之于千里之外。在疗养院,他按部就班并且礼貌地对人,“避免表露任何情绪”,作为一种与人们保持距离的策略。他不喜欢与人亲近,怕生,“用沉默将自己包裹起来”。但一旦气氛融洽,他也能融入其中并感到惬意。泽利希带他去自己的一位朋友家里,瓦尔泽起先感到手足无措,但泽利希朋友一家人的热情好客终于使他放松了下来。
未进到疗养院的瓦尔泽工作不多,只为赚到能够写诗的自由。进到疗养院之后,他说,我是来发疯的,在这时候,他也放弃了情感的负担。或者说,将情感的负担连同那个敏感的诗人一起潜藏了起来。“1月7日,罗伯特的姐姐莉萨在伯尔尼去世。就我对他的了解,他宁肯咬断舌头也不愿意谈起姐姐的死。”莉萨是一直照顾他的亲人,瓦尔泽曾经以莉萨为原型写就了《坦纳兄妹》,然而对于姐姐病重与离世的消息,他一直没有多说什么。同样没有多说什么的,也有对于兄长卡尔的离世。
瓦尔泽也许是一个感受到人世沉重的人吧,他有着鄙弃世俗的一面,但也有包容地看待世界好与坏的一面。比起人世,他更渴望自然,也渴望美好与高贵,却也绝对不与日常疏远:“日常事物已足够美丽和丰富,从中可以迸射出诗意的火花。他也喜欢食物,喜欢草地、森林以及宁静的房子。这些东西在他那“星期天的会客室”里实现了。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笨蛋。”罗伯特·瓦尔泽最终一个人倒在了雪地里,积雪掩盖了他倒下的声音,也吸收了他心跳的声音。人们在他的旧皮鞋盒里发现了五百多页手稿,字母均一二毫米,用铅笔写在车票、日历、烟盒上。瓦尔泽喜欢在雪地上行走,他把雪花带进了旧鞋盒——就像他避免表露的情绪,写在世俗的备忘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