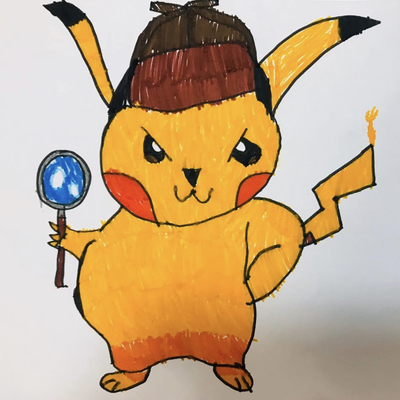几点思考
“白马之盟”是一种对秦制的偏离,因为它没有能够形成稳固的皇帝—贵族—平民(农奴)式的封建体制。//这个句子意思不太对劲。“因为”应该是“而且”吧。
秦制社会崩溃的第二点原因: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个人认为这个表述不够精确。应该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发生分裂”。秦制社会有三方力量,皇权、官僚和平民。皇权的统治基础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内部呈分裂状态才是皇权乐意看到的,所以历代帝王才会不遗余力打击朋党,因为官僚呈散沙态才无法与皇权角力,扁平化才能如臂使指执行帝王意志,才能提升汲取的效率。“明亡,亡于党争”,与其归罪于“阉党”或“东林党”,不如说是皇权失去了对其统治基础的官僚集团的控制所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后半句是事实。实际上,当朱元璋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又没有发明制衡官僚集团的制度之时,已然埋下了种种祸根,这也是明朝宦官乱政的根源,因为皇权需要引入第三种力量来制衡抱团的官僚集团-内阁。雍正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私人咨询团队军机处取代了建制化的内阁,秘折制让地方督抚互相监督而分裂。清朝皇帝对官僚的定位非常符合秦制社会:官僚就是帮助皇权进行汲取的家奴。对官僚,如果过分刻薄寡恩或是过分清廉公正,不给官僚任何甜头,则要么官僚消极怠工,要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玩插边球来牟利,总之都影响汲取效率;皇权统治的艺术,就是让官僚高效汲取民脂民膏,让平民尽力供给民脂民膏,二者都不得抱团以威胁皇权。
秦朝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用官僚集团取代世袭贵族。世袭贵族,曾经作为可以制约君主的力量,并非一夜之间就消失的,世袭贵族力量的消失几乎是和君主独裁权力的膨胀同时发生的。秦制如何驯服贵族力量,不仅仅只有一个白马之盟。仅仅是如何控制藩王的力量,就发生过“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等;因军功而获得爵位者,特别是所谓的开国功臣,不同朝代不同君王是如何控制分化这些可能威胁皇权的贵族力量的?
人事权是君王控制官僚集团的关键,文中并未系统论述,秦以辟田、军功选官,汉有察举、征辟,隋唐以后有科举。正如文中所述,即便是科举时代,由科举入仕从来都没有占据绝对,其他如恩荫,卖官等还有多种手段,不同朝代的君主是如何使用这些组合拳来控制官僚集团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哪些方式能得到皇权的青睐?是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知识经验?还是某些方式有着特殊的内因而能大行其道,比如科举。
缺乏对秦制的动力和目的阐述,文中似乎都笼统归于不受约束的欲望,可是,秦始皇汲取的动力毕竟和万历皇帝汲取的动力天差地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体,对汲取的动力、目的、手段和尺度都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不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文明的进化还是倒退?是制度的更新还是历史的轮回?
缺乏对制衡的力量的系统叙述。文中充满悲观的气氛,皇权无可战胜,无任何制衡的力量。只要君王能把握汲取的限度,掌握统治的艺术,有效是社会成原子化状态,则无任何力量制衡皇权的绝对力量。然而,现实是皇权,官僚和有组织能力的乡绅之间的角力此起彼伏从未断绝,魏晋门阀大族,北宋的文人集团和朋党论,明代朝中有内阁朝外各种书院讲学兴盛,都是这种角力的具体体现。此外,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虽然在现实中大受打击,然而其深得人心的力量因为不可小觑,可以说是君王的一道紧箍咒。朱元璋之所以收回“罢配享”的成命,可不是因为钱唐个人的冒死抗议,钱唐死一百次都不足以让这个冷血嗜杀成性之辈皱一下眉,朱元璋是看到了开罪整个士人集团(也就是其统治的基础)的风险。秦制的法家思想,其死敌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君主独裁无法抛弃“外儒”的外衣,也会无法取下头上的金箍。
整体而言,本书围绕秦制社会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和发展演化展开,其论述大体以时间线为轴论述,从秦朝讲到辛亥。然而,三角关系的三方,制裁与反制的手段,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交战与交融,并未得到全面系统的论述,以致全文有落入说书人抖包袱讲故事的俗套的嫌疑。
本文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对三角结构中处于弱势和被盘剥地位的平民的深切同情,毫不留情的揭开了历史上所谓的太平盛世的虚幻面纱,露出了秦制社会残酷无情虚伪的一面,所谓的千古一帝万世功绩,无一不是避实就虚的粉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