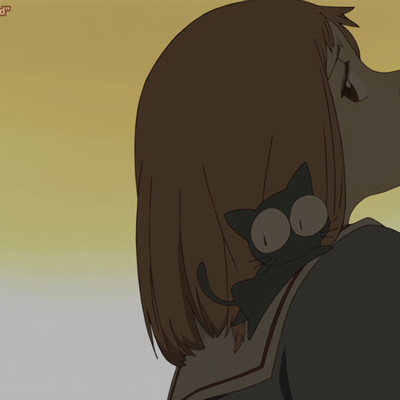藤本树的电影梦应当悬置
《蓦然回首》是电影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对电影就本体论上进行检讨,这里给出两种方向:1)电影是运动与时间;2)电影是文本与符号。我认为,2)是电影的阐释,1)才是电影本身。
而在藤本树与电影的问题上,一般将藤本树与电影联系起来的讨论往往集中在2)的层次。文本上,《炎拳》《再见,绘梨》中的电影元写作,符号上,除了在叙事框架上已经出现电影元素的上述作品,《电锯人》也将电影作为符号之一种。而在影视改编中,《电锯人》动画的 OP 画面也 neta 了诸多藤本树品味的电影场景。然而,我们将文本与符号归属给电影的前提,应当是眼前的作品已经是一部电影;否则,多元的体裁与艺术形态也能承载文本与符号,仅仅有文本与符号并不成一段影像为电影。更极端地,纯粹的蒙太奇拼贴艺术或许适于在美术馆的放映机上轮播,却难以成为电影占据观众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段。至于本片也同样使用的元写作技巧,应当看到,并不是一部拥有如此手艺的作品便当然成为电影。
运动与时间才是电影的本体所在。在漫改电影中,因为运动与时间的匮乏而难以被视为电影的例子实在过于普遍。并不是一段动起来的、适于一般影院放映时长的动-画便是电影,场面调度的匮乏已经不足以批评这类影像作品,它们与静画的播映可区分之处寥寥——或者通俗地说,PPT 电影。本片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藤野回忆与京本过往的蒙太奇便完全落在这样的批评里。 而即便不论这段处理,本片的场面调度上,有“电影感”的地方又也寥寥,藤野与京本拉手时的对切或算一例,但这预告片中即出现的场景,又在正片中出现了两次,即便这段倾注了创作者的心血,但在时长本就局限的前提下反复出现总是令人厌烦;藤野首次被京本夸赞后的雨中雀跃可算另一例,但这就牵涉到另一处问题:为什么这段但挑出来处理得不错的表现,其力度甚或反而不足漫画原作?
藤本树的绘画特色之一,在于用不自然的肢体动作与面部特写表现充沛的情感。 在漫画原作的雨中情感释放一幕中(甚至不知道用什么动词来指称那一幕为好),怪异的动作与表情会让不知晓上下文的读者将其视作符号而 meme 化而传播,但这一张跨页又不仅是符号而已。这一幕可以无可置疑地被放入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所界分的运动之子分类情动之中(Affect)。进一步的,德勒兹是通过对特写镜头的分析展开的对情动的分析,而藤本树所擅长的也恰恰是特写——在藤本树作品中,动作与分镜可谓都不出彩,但特写让其从情动的角度进入了运动-影像。又,德勒兹在《时间-影像》的分析中,又提出了“晶体”的概念,认为晶体“不分割时间,它主要是颠倒时间对运动的从属关系”,从这一层来说,连接可能世界的藤野与京本的那张四格漫画便是包含情动的晶体,这拯救了整部片子,让它没有被排除在“电影”的范畴之外。
然而,拯救电影的“情动”与“晶体”却统统来自原作,而非电影改编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蓦然回首》漫画原作比电影改编更加“电影”一些。然而,这个结论却并不主要指向对电影改编的批评,而是说:藤本树作品中,切合电影本体论特征的要素恰恰使得其不适于被改编为电影。凝固在一格漫画中的不自然的动作能够成为饱含情感的一帧,但如果在连续动作的影像序贯中,如果不是被夸张地反复强调表现(这是漫改电影,无论是实写化还是动画化,都常落入庸俗的窠臼),就是在掩藏在一系列动作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在此处的动画化改编中,尽管不如漫画原作有冲击力,却至少在朝着电影的方向在努力,而不是为了还原“名场面”而被漫画的体裁拘束。人像特写的问题则在于,首先,技术与成本上,一部动画化电影在实践上还原特写;而在艺术处理上,特写的取景框容易达成,特写包含的情动却难以在动画中实现。
这样的情况归结下来便是,藤本树漫画中的电影感,使得其动画化电影改编距离电影感反而更加遥远,这是藤本树是作品的内在困难与张力。除非未来有更加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否则藤本树的电影梦可能须得长久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