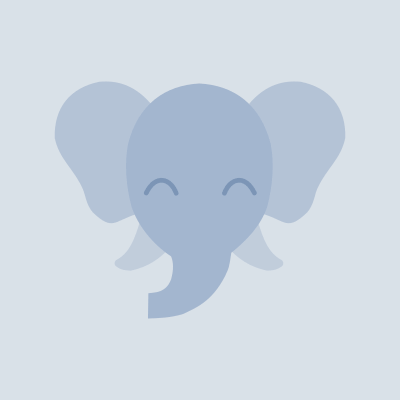来自微博 梁州Zz
看到#开幕式有自己的燃冬#这个tag,简单聊聊为什么巴黎奥运会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用这样一个奔跑的镜头致敬特吕弗的《祖与占》。作为特吕弗的代表作,《祖与占》其所蕴含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三人行”这么简单。
《祖与占》是特吕弗个人创作史中最具有反叛精神的新浪潮作品,更是新浪潮电影的重要篇目。“两男一女三人行”的经典画面,在一个世纪以前,象征的是一种仿若乌托邦的个人选择,它代表着世俗意义之外的自由、狂野,与通往四面八方的流动的情感。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与文学、绘画、音乐都有所不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电影是最不具备文化门槛的一种——它不需要文化准备,不需要识字,具有大众化,在默片时代,聋哑人与普通人一样,享受着同等的观影乐趣。
默片时代,导演通过运用流眼泪的镜头来代表哭声,碎片代表观众没有听见却存在于现实中的盘子落地被摔碎的声音。电影作为现实的渐近线,自它诞生以来,则具有其独特的、非常明晰的表现力。
两百年前,17世纪的法国开始了启蒙运动,“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我们应当用理性之光将黑暗的人们引向光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口号因此而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开始进入了新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战争后,整个欧洲都处于灾后重建的心理状态与选择下,彼时的人们被巨大的物理化伤害笼罩着。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的迭代与进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因为消炎药与抗生素的发明,在物理意义上不容易消亡,但在精神上却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成为许多科幻片的现实基础。
此时的人类文明与斗争,无一不进入白热化的发展阶段,先锋艺术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呈现在外。
第二次世界战争开始后,人类文明中的电影又一次迭代。诞生于好莱坞的歌舞片开始形成类型片,也拥有了其固定的观众——战争中留守后方的孩子妇女、老人。作为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在战争与文明的更迭中不断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它所蕴含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一种现实与时代的投射,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从一个国家流浪到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流亡到一个世纪。
战争带来的世界格局重组与技术革新,使得流浪的电影第一次系统性地开始形成工业。好莱坞电影在这个时期正式诞生与确立,电影由此进入“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人类文明也快步行进着进入了60年代。战后的二十年,有声片为好莱坞带来巨大的利益,电影作为一种盈利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历史中正式与人类文明的叙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英语中的“film”,象征着可见、可听、感人的叙事电影,而娱乐性的电影也有了其名谓——也即是movie。
一个世纪后的大众,在灾后重建的世界中,真正对电影艺术、媒介艺术的特性有了统一的认识。语言学、符号学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电影。电影也正式地成为了大众文化中最重要的表达部分,美国电影工业的确认,使得好莱坞之外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电影,都在做同一件事——为打破好莱坞电影的思维模式僵化而努力。
1958年,新浪潮电影正式产生于法国。以安德烈·巴赞为首的《电影手册》青年编辑人员等,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反对过去影片中的“僵化状态”,强调拍摄具有导演“个人风格”的影评。
巴赞那句“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也诞生于此。
新浪潮思潮的伟大,不仅在于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它的开拓性,在于上个世纪的艺术家与导演们,第一次如此清晰且明确地期望以电影的拍摄手法刻意描绘现代都市人的处境、心理、爱情与性关系,与传统影片充满主观性与抒情性的“演绎”不同,它强调人根本的生活,采用实景拍摄,主张即兴创作。
“我本是我”,“我亦是我”。讲故事,更讲身处于现代性中的人的困惑,现世的困惑。
而特吕弗的《祖与占》,则是新浪潮电影中的“翘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应当如何应对感情中的自我?当我以为我伸出手即是触碰爱情,当我以为我按下选择的按钮即是抉择生命,命运会告诉我现实的荒诞与偶然性。哪怕我蔑视道德,随心所欲地跳脱尘世,打破以往的规则体系,我仍然虚无,找不到自我。
特吕弗不给予观众答案,他只提供视角与一种记录。当自身无法再由传统结构与社会给予我们的教化中获得意义,反叛还能塑造自我吗?
《祖与占》中飞落长桥的轿车,像是一串连绵的省略号。一如生活,to be or not to be,痛苦与快乐,我们是亲历者,也只能在反叛与诚实地面对自我中经历着生活的颓唐与雀跃。
1957年,新浪潮正式开始以前,1864公里外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内,加缪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发表了那篇举世闻名的演讲——
“在二十多年的荒诞历程中,孤立无援的我和同代人一样,迷失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 仅靠内心隐隐的一种感觉支撑着:在当今这个世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这一行为肩负使命,并迫使你不仅仅去写作。它尤其迫使我按我自己的方式,以我的一己之力,与所有和我一样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起去承担起我们共有的那种痛苦与希冀。”
“这些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浪潮掀起时,他们又正值二十多岁。接着,像是要使他们的经历更加完整,他们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经历了那个满目疮痍、遍地集中营和牢狱的欧洲,而如今,正是他们这些人,又要在毁灭性核武器的威胁下,抚育他们的下一代,完成他们的使命。”
“我想,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他们不断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只是因为与日俱增的绝望,而做出了耻辱之举,并且堕入了这个时代所盛行的虚无主义。但是,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整个欧洲,我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虚无主义,仍在寻找一种正义。我们需要锻造一种在多事之秋生活的艺术,为的是能够涅槃重生,然后坦然地与那历史进程中的死亡本能作斗争。”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世界的彼端,回望塞纳河畔上升起的雕塑与画像,那些象征着人类文明结晶的艺术载体——艺术从不是一场孤独的狂欢,它是一种手段,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同的苦难与欢乐,从而影响着无数代人,使我们不再自我孤立,从而屈从于一种最为质朴、最为普世的真理中。
真理或许灰暗,或许无以为继,但忠诚自我的生活之树,永远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