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文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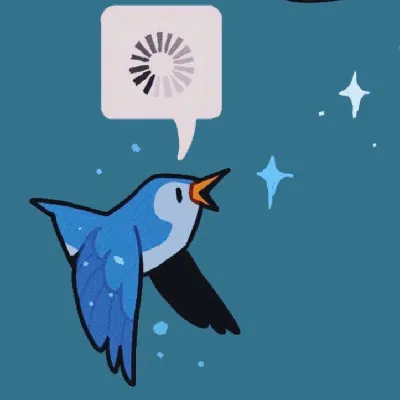
大多数人都熟悉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
我们用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症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这个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一致。
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以及为了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错综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引发神经症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
对恐惧与焦虑做出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试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没有用的。他之所以焦虑,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情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摆脱焦虑的方法:一是把焦虑合理化,二是否认焦虑,三是麻痹自己,四是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情境。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尝试用四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它们是:爱、顺从、权力和回避。
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防御机制对他人格的影响就越大,他想不到或不能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体力、智力或教育背景,完全有理由期望他完成这些事情。总之,神经症越是严重,抑制作用就越多,这些抑制作用既微妙又强大。
真正的爱和对爱的神经症需求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首要的情感是对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觉是次要的。
崇拜或爱可以用来掩饰挫败别人的冲动,具体方法如下:通过使破坏性冲动藏于无意识中不为自己所知;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制造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通过替代性地享受成功或与其分享成功;通过安抚竞争对手从而避免他的报复。
由于我们的文化相信,除了爱情,男人在其他方面都比女人优越,所以男人身上的这种态度,很少需要借助崇拜来加以掩盖。它通常公开、直接地表现出来,对女人的工作和利益造成损害。
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是女性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而且实际上是她们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坚信,如果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成就;而女人们则认识到,通过爱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名誉。这种文化角度的差异,对男女的心理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讨论这种影响有点不合时宜,但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把爱当作一种策略。与此同时,这种关于爱的主观信念,又使她们的要求变得合情合理。
人们性欲的增强,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当作一个发泄途径,用来缓解焦虑和被压抑的精神紧张。
很多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事实上跟性欲几乎没有关系,而只是想要寻求安全感罢了。
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不辞劳苦地赋予了性以应有的重要性。
爱,不管它还意味着什么,始终意味着屈服,屈服于自己的情感,屈服于自己的爱人。
性高潮的前提正是完全放弃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知道“放弃自我”带来的满足感。在身体或精神紧张后进入睡眠的过程中,甚至是在进入麻醉状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忘我的满足。这一效果也可以由酒精所引发。在使用酒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之所以感到满足,失去抑制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减轻悲伤和焦虑是另一个因素。但是,它最终的目标还是获得忘我和放纵的满足。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让自己沉浸于一些强烈的感觉中可以带来满足感,无论这种感觉是源于爱、大自然、音乐、对事业的热情,还是性放纵。
更广泛地说,人类生命中一个固有的事实是,个体是有限的、孤独的——他所能理解、完成或享受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说他孤独,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与自己的同胞和周围的自然都是分离的。事实上,这种个体的局限和孤立,正是大多数寻求忘我和放纵的文化试图克服的。我们可以在《奥义书》(Upanishad)中,也可以从无数条河流汇入大海、失去自己的名字和形状这一画面中,看到对于这种追求的最恰当、最优美的表达。通过让自我消解于某种更大的事物,通过成为一个更大实体的一部分,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有限性。就像《奥义书》中所说:“通过化为虚无,我们成了宇宙创造之源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宗教供给人类的最大安慰和满足:通过失去自我,他们就可以与上帝或自然合一。此外,通过献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同样能够获得这种满足;因为把自己交给某一项事业,我们便感到与一个更大的整体合而为一了。
感觉自己被遗弃在黑暗和海浪之中并与其融为一体。这种倾向,可以存在于被催眠的愿望中,存在于对神秘主义的喜好中,存在于虚幻不真实的感觉中,存在于对睡眠的过度需求中,存在于对疾病、疯癫和死亡的渴望中。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各种不同的受虐幻想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受他人主宰、任他人摆布的感觉,被剥夺了一切意志与力量的感觉,完全屈服于他人统治与支配的感觉。当然,每一种不同的表现都有其特定的方式和自身的内涵。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只是感到受伤害的普遍倾向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对奴役他人的冲动的防御,也是一种对他人不被自己支配的控诉。但是,除了这种建立防御和表达敌意的价值,它还暗含了一种放弃自我的正面价值。
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神往,另一个原因是它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不仅别人会根据我们取得的成就来评价我们,就连我们自己,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会遵循这种模式来评价自己。根据当前的社会文化,成功来自我们自身固有的优点,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实际上,成功取决于许多受我们控制之外的因素——天时地利的环境,不择手段的冒险,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在当前社会文化的压力下,即使是最正常的人,也会在成功时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而在失败时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不用说,这反映了我们的自尊搭建在摇摇欲坠的根基之上。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激发了一种对爱的强烈需求,将其作为一种补偿。获得爱,会使一个人感到不那么孤独,较少受到敌意的威胁,对自我也更加确定。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它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但就像成功一样,它也成了一个幻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爱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是一种掩饰,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由于我们对爱的期望远超过它可能实现的程度,所以它被弄成了一种错觉。社会文化对爱的强调,掩盖了导致我们对爱产生夸大需求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我所指的仍然是正常人——陷入了需要大量的爱但又难以得到爱的困境。
“霍妮的个人问题诱使她开始探索自我理解,这方面的记录起先包含在她的日记中,后来则见于她撰写的精神分析著作之中。”霍妮无法将自己的问题永久地压抑下去,把它们全部留给自己,因此她的著作就是“隐秘的自传”。
“霍妮的真知灼见来自于她为减轻自身与患者之痛苦所做的努力。如果她的痛苦不那么强烈的话,那她的洞察也不会那么深刻。”
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患者获得知识或领悟,而是让他利用这种领悟来改变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