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紧的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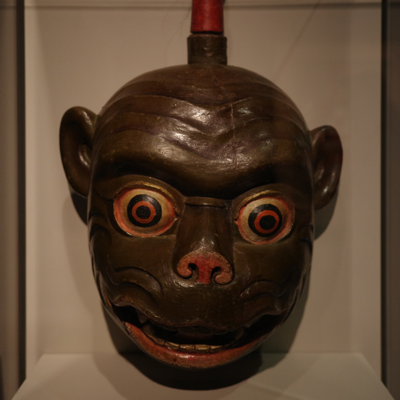
V.S.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讲述的是特立尼达印度移民毕司沃斯先生想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故事。整部小说的情节可以以几个标志性事件来串联,从毕司沃斯先生的出生,和莎玛结婚搬入哈努曼大宅,搬出大宅在捕猎村开店,受骗被迫迁往绿谷做监工,第一次试图建房失败搬回图尔斯家,到举家搬迁到西班牙港和莎玛的姐妹同住,开始报社记者工作,参加社区工作,买下自己的房子,不久意外因为心脏病去世结尾。
小说描述聒噪的印度浮世绘是有趣的,但基调确实令人沮丧。具有做作的宝莱坞戏剧特质的语言:妙语连珠、旁征博引、惯于争鸣,最好还有一丝异域风情。“借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小说中有众多的‘也许’和遗憾,极为接近现实。希望之后的打击,岁月的流逝,生活的消逝,然后揭示白费的辛苦;‘哦,我可怜的马蒂尔达!但是那挂项链是假的!’”那婆罗门装腔作势的感觉或许还与维多利亚朝的贵族相似。毕司沃斯先生用科林斯清楚印刷之莎士比亚戏剧给孩子取名,在和连襟比较的时候拿马可奥勒留的哲学书充点门面,阿南德被狄更斯小说中掺水的白兰地的描述所引诱,于是为了这文学色彩把那讨人嫌的东西喝了下去……这都是些滑稽的场景,但是若读者不是完全没心没肺,恐怕都没法完全把自己投入这种欢笑之中,因为她太沉重、太复杂了。如同莫里斯《七个铜板》里“笑得那么甜蜜,笑得流眼泪,有时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妈妈一样,处在挣扎着生活的中的主人公们除了打心坎里笑他们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毕司沃斯先生是个绝望的人,这一点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图尔斯大宅里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局外人,但他的绝望始终不代表轻言放弃。这一点与奈保尔后期小说《浮生》或是贝克特“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的表述是不同的。一所自己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所做的都是为了这所房子,为此他一直生活在别处。一开始他认为娶了莎玛便是新生活的开始,从此他开始等待,“不单单是等待爱情,还希望整个世界带给他甜蜜和浪漫。”但是他没有预想到图尔斯大宅的自命不凡将与他的心高气傲格格不入。在没有知心朋友,每天与连襟拌嘴的日子里,他发现自己需要一方留存给自己和家人的土地,得到这块土地不仅证明了自己,也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何等难以获取。当他认为简单的梦想一次次破碎在生命中的时候,他开始绝望。“每一种认识都姗姗来迟,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惊讶,那只是一种他早已接受的状态。” “他沉溺在绝望中,在想象里,那就好象沉浸在代表着他还没有经历的生活的虚空之中。一夜又一夜,他沉溺着。但是他不再有质讯中的惊慌,不再有愤懑梗在心中。他只是发现自己非常不情愿,他原来害怕退缩带来的后果,现在却始终麻木着。”他变得“烦闷易怒”甚至“丑陋”。生活一直是一种期待、一种准备。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没办法期待些什么了。毕司沃斯先生无疑是坚韧的,坚韧到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程度。在捕猎村开店的时候他们的店面同时也是家,那间店铺墙壁倾斜下陷,很多地方墙皮剥落,很容易松动摇晃,但是其中的干草和竹篾却使之具有一种惊人的弹性。毕司沃斯先生很像这堵墙,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并且外部世界总对他有太多的冲击,他却一直坚持下去。这又是毕司沃斯先生的悲剧,在于他为了获得独立,和自己较上了劲,“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推迟了所有的快乐。”而《浮生》中的威利则做了另一种选择,如同奈保尔中年游历印度突然发现了“完整的自我意识”一般,他自以为是、对批评漠然无动于衷;岁月流逝他意识到“他们(年轻人)在表白他们是谁,为此甘冒一切危险。……我什么险也没有冒,而现在,我人生中最好的部分已经过去。”
然而,充满雄心如毕司沃斯先生,似乎也预感到自己没有办法获得自己梦想中的生活,这或许也是当时尚且年轻的奈保尔个人的梦魇。在奈保尔的生命里,有一个无法跳出的牢笼——父与子的轮回。奈保尔与父亲的关系虽然不像毕司沃斯先生与阿南德一样,但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这个问题,却是贯穿了奈保尔的创作的。毕司沃斯先生对阿南德说: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阿南德理解他的用心。父亲和儿子,互相都认为对方是软弱无能的,互相都觉得自己对对方负有责任,这在某些极为痛苦的时刻,使得一方过于夸大对方的权威,另一方则过于毕恭毕敬。同样,在《浮生》里,父亲面对郁塞不解的儿子,心里想的是另一番话,“我曾以为你是我,我曾担忧我对不住你。但现在我知道你不是我了。我脑子里的东西并不在你的脑子里。你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担忧你,则是因为你走的是我一无所知的路。” 于是儿子不论是否像父亲,父子两人都心存担忧,并且对于彼此的发展不感到乐观。这与加缪《局外人》中的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里修女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
从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认为奈保尔在叙述这些部分的时候使用了自己的经历,他是一个反刍的作家。然而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的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于,虽然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到最后作家也许一生都在回味不知起点在何处的自己的生活,想要逃离预设的生活,最终又步入了陷阱。在《幽黯国度》里出现的初来乍到孟买,对贫穷的小男孩的情况表达义愤的奈保尔自己,与米格尔街上的简单地认为这是贫民窟外来者何其相似!特里林说过“一部伟大的史册的特点是我们迟早会像感到历史学家所叙述的事件那样感知到他本人。”小说又何尝不是呢?永不满足,并且永远感到自卑。这是阿南德。而阿南德的这种性格来自父亲毕司沃斯先生,他在学习父亲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嘲讽。“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迅疾的、深刻的轻蔑态度,这成为了他天性的一部分。这使他不能从善如流,使他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长久的孤独,但是也使他所向无敌。”这个自卑又自视甚高的阿南德,也许就是早年留学英国的孤独自傲的奈保尔呢。
除了这些贯穿他创作生涯的问题,《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还有对于浪漫的享受的疑惑。毕司沃斯先生喜欢文学,这在实干氛围的图尔斯家族里是不被看好的,因为这实在是种“不切实际”的东西,“即使他的哲学书能给他一些安慰,他却始终摆脱不掉那种它们和他的处境不相关的感觉。”事实上,让殖民地人民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像毕司沃斯先生这样敏感的人是会懂得欣赏艺术的美感的,然而这种享受是否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出身贫困的大众接受了这种教育,是否会产生尴尬?奈保尔只是描述,并没有作答。评论家常说奈保尔的文字是无根的,或许正因为没有立场批判,所以他始终寻找更为深入更为灵活的解决方式,看问题也无法很快下结论。这也许是他之后作品中对于后殖民时代摆脱殖民者影响的思考的先声了。
并不是没有恬静、美丽的瞬间的,在这许多焦虑之外。当毕司沃斯先生在绿谷的一天傍晚,他感到非常平静。他意识到他一直觉得自己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而一种暂时的生活是没有办法被严肃对待的。于是他决定自此以后把所有的时间都视作珍贵的,不将被虚度的。这顿悟是绚丽的,几乎让人感到无法呼吸一般。而她的不可持久性更使她珍贵,在这之后毕司沃斯先生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躁狂之中,只因为他所熟悉的漫不经心的却目的性太强的生活离他而去,而他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实实在在的又出乎意料的甜蜜与温馨,之前是被无情忽略的。他把所有心血花在儿子阿南德身上,忘了还有曾经让他欣喜的女儿赛薇,儿子出国留学之后对他不甚关心,这时候赛薇在他面前绽放了。“他种了一棵蝴蝶兰。他的树又开花了;生长得这样迅速的树能开出这样甜美的花朵不是很奇特吗?”可是如果阿南德回来的话,毕司沃斯还看得到赛薇吗?对于这个“永远不能满足”的人来说,什么才能让他平静下来呢。
就像舒尔茨所说的那样:“童年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事,我们只是一再回到原点,不断挣扎但没有结果。灵魂把自己打在里面的那个结,并不是一个你把两端一拉就解开的假结。相反,它收得更紧。”与天命相博了一生,却发现套在自己脖子上本应该解开的的人生的枷锁越绞越紧。
最后会怎么样呢,“于是后来,当各种痛苦笼罩之下的安全的时刻,当记忆不会刺伤他们的时候,他们带着欢乐或者痛苦,极为缓慢地陷入过去的岁月中。”
“而一旦他们不再挑剔,这房子也就成为他们的房子了。”
(20岁的小猿宝的写作风格居然是这样的哇!大猿宝今天发现这一篇,决定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