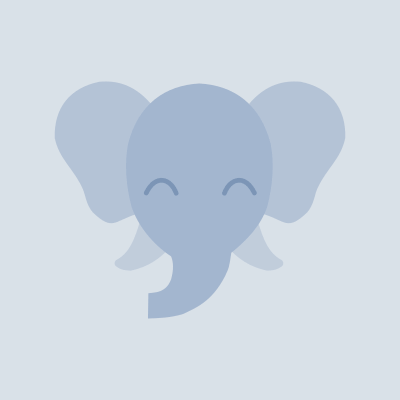对于现代性的一点误读
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无论这种叙事是直白地使用「进步」这样的词汇,还是隐藏在「东方主义」的想象当中——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放开西方学术界使用的话语体系,完全从本土经验出发,重构理解本土经验的叙事,继而从中寻找到突破的可能性。罗雅琳在《上升的大地》中意图完成的就是这件事情,中国乡土经验为切入点,以多部关于中国乡土经验的文本为材料,试图找到「中国乡土经验」与「现代性」相通之处。为此,作者需要完成两个工作:一、识别文本中呈现的中国乡土经验;二、探索中国乡土经验与现代性之间可能的连接;亦如本书导言所言:
在我们意识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的‘乡土中国’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将‘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连接起来?xxi
罗雅琳选择了五组相关文本,分别是:一、1930 - 1940 年代间关于西北的旅行、报告文学;二、《黄河大合唱》;三、《平凡的世界》;四、当下社会对于农村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五、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
在识别这五组文本中展现的中国乡土形象时,作者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展现了这些文本在创作时隐含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而仔细辨别。大体上,作者拒绝带着先入为主来观察乡村的视角。她认为,这种视角就好比带着滤镜,不仅无视了中国乡村真正的现实,甚至可能会产生盲目的误用。这一点,在前述的第一组和第四组文本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论述。
讨论 1930 - 1940 年代间关于西北的旅行、报告文学时,作者选用的对比是范长江、陈学昭与爱德华·斯诺。范与陈带着救亡图存之心前往西北考察,然而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依然停留在西方的模式上,坚船利炮、政治制度、文学心理,因而时时将他们在西北所见与西方模式比对。凡无法匹配,就贬为原始落后;而有近似之处,则认为是进步的源泉,例如当他们见到西北女性民风更为强悍时,就认为他们更符合西方男女平等的理念——殊不知,这只是对于中国乡村的误读。
相较之下,作者更为认同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呈现的中国乡土景象。她认为,斯诺超越了当时西方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即由传统儒道所塑造的消极、刻板、矇昧的形象,进而展现出了更为乐观的革命者状态。
斯诺书写了一批具有愉快精神面貌的中国革命者,他们使落后的西部中国呈现出一种真正的‘现代’的形象,也为在落后环境下展开的抗日战争带来的胜利的信心。这不仅是一种书写经验的策略,更是对革命所创造的新文化和新历史的形象呈现。32
同样的结论也出现在对当下社会对于农村的「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当中。这一次,作者剖析的文本来自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记》。这两部作品分别是梁鸿对于自己河南家乡梁庄、以及对于从梁庄走出来的打工者的观察。尽管梁鸿自身带着一种悲切的心理去观察自己成长的源头,但是正因为她早年就离开家乡,浸润在城市生活中已久,将城市的生活标准加于乡村之上,因此难以避免地将乡村看成一种落后。而在落后中寻找到的也只能是落后。
至此,罗雅琳在本书中的第一个工作已经完成。大体上,她认为在过去百年来的中国乡土经验文本中,许多人的观察带有强烈的偏见。他们要么以发展主义的眼光看待乡村,认为乡村注定处在原始、矇昧的状态当中,要么用浪漫化的手法去描绘乡村,构想出一种田园化、自然化的风光,进而用中国乡村的衰败做对比。这两种状态都好比是将乡村封死。乡村应该作为博物馆中的展品而存在,而不具备任何在现代社会中存活的意义。
反之,正如罗雅琳在《红星照耀中国》《平凡的世界》以及刘慈欣科幻作品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乡村依然存在一种昂扬振奋的精神状态。
(《平凡的世界》)意味着农村人并不会因为经济水平的落后而缺乏获得‘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艰难困苦为他们提供了磨砺精神的必要条件。那个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形象,因此才无比激励人心,成为激励了一代代农村青年的形象。在农村和农民被视为‘愚昧’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路遥为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农村青年找到的通往高贵的道路。92
刘慈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成为英雄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技术如何高超,而在于他们的眼光超越了目前的生存困境,能够展望遥远的未来,为人类和共同体作出长远的谋划……这些人的努力也许一时失败了,却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勇气和希望,使他们为共同体的幸福和发展前仆后继。150-151
但问题是,这样就是中国乡土经验与现代性相通之处了吗?
「现代性」或许是个极其容易被误读的词。它就如同「启蒙」「理性」等词汇一样,有时人们在使用他们的时候能够取得大体的共识,但依旧充满分歧。罗雅琳自己也在书中说,
‘中国乡土的现代性’首先也不应当被定义,而是在中国人的经验变迁中、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中呈现其自身的特殊品质。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回答是不能让人满意的。「特殊品质」由谁来识别?识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定先入为主的判断标准?放在本书的语境中,为什么乐观愉快昂扬的精神状态为作者所看中,而其他的品质诸如安于天命、家庭和睦就不为作者所看中,因而没有被纳入到「上升的大地」的命题当中?
或许,作者可能的一种回答是,「上升」一词本来就隐含着此刻与彼岸之间的差异,因而昂扬的状态意味着改变的可能性,而安于天命的状态则意味着停滞。不过,当作者在引用尼采塑造「上升的大地」的命题中,其实也暗含了新的标准。当尼采在讨论超越时,他建构了一整套关于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理论,并基于此才能展开超越的理念。因此,当罗雅琳援引尼采,提出上升的理念,却没有给予她自己的标准,这多少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或许,罗雅琳亦曾暗示这个标准的形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条道路、和另一种普遍性」,在论及刘慈欣的时候,罗雅琳反复提及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正是帮助人们想象新的可能性,而她对于刘慈欣的赞誉似乎正说明,她想自中国乡土找寻的现代性也正是这种可能性。
但这可能是一个更危险的命题。首先,在想象资本主义之外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难以避免需要去触及物质、制度等各个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精神状态之上。全书中,罗雅琳亦偶有超越精神状态的讨论,例如在反驳梁鸿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论述时,她援引了贺雪峰的社会学调查,指出农村留守老人的农业劳作是半生产半休闲性质的(118),因而指出梁鸿的论述只是一种伤逝,而非完整的体认。
而一旦引入了更广泛的实证研究,超越了文本本身,就难以避免进入更为复杂的经验世界。贺雪峰对于农村的调研涉及多个面向。老人农业方面而言,贺雪峰自己亦曾表示,老人农业的半生产半休闲性质取决于老人的年龄和劳动能力,75 岁以上老人基本是断无可能用休闲的心态去面对劳作的。此外,农村老人虽然物质上可能还算满足,但是精神空虚亦是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农村老人的经济保障也并不充分。如果将贺雪峰的上述判断加入其中,罗雅琳援引贺雪峰来说明半生产半休闲性质的做法,是否存在一定的浪漫化乡村的嫌疑?这似乎与她对于梁鸿的批评并无二致。
此外,如果文学经验可以被社会学经验所反驳,那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否能够成立?我们是否需要援引更多史学界对于延安时期的研究,来判断《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于延安的描述是否准确?当出现出入的时候,我们又要如何理解斯诺所赞扬的那种昂扬乐观的革命精神?这些问题似乎都会让将中国乡土经验与现代性勾连的努力遭遇更多的挑战。
关于经验,我们所能知道的即是人的经验是极其复杂、且多面向的。任何一种文本所代表的经验,也可能为另一种经验所削弱和抹杀。我们或许没有必要走到极端,宣称所有经验都是完全主观的,进而否认经验能够指导现实的可能性。但我们同样也需要警惕过于强调部分经验的意义,进而将其放大至现代性、道路、世界的意义上。正如刘慈欣或许是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小说背景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在创造性地容纳第三世界经验。
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基于本土经验,寻找现代性可能性」这个命题,我个人同情新儒家的尝试,也认同重新叙事来理解历史的努力,如宋念申的《寻找东亚》。但要完成这个命题,需要的是对于本土经验以及现代性可能性更为全面的理解,因而,「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这个命题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期待。我认同也喜欢本书中众多的文本分析思路。但书中提出的现代性想象是否真的代表现代性?我暂时还无法认同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