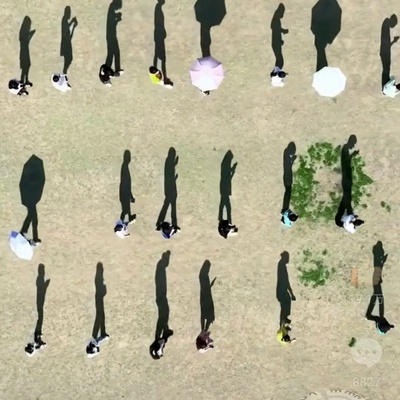艾柯的界限 —— 对于艾柯阐释理论的一个文化研究式的回应
引言
1781年,康德首次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里,他试图建立一个理性的法则,将我们的知性限制在感性的范围内,以克服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同样,在当代文学理论当中,也存在着关于解释和读者角色的争论,艾柯追随康德的脚步,以皮尔斯“无限符号”的预设为基础,提出了如何限制解释范围的问题,皮尔斯引发了欧陆哲学传统中的解构主义运动,以克服来自索绪尔和结构主义的束缚。在1992年的演讲《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艾柯与其他学者就这个主题进行了辩论,他们的贡献非常丰富。在本文中,我将通过扩大语境从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话语进入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探讨这个问题如何在文化研究领域得到回答,以及如何回应艾柯的叙述。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这场理论争论进行了简短的语境化,展示了符号学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确定了艾柯对话的语境和对象,并重建了艾柯的解释理论,用与皮尔斯的密切联系来说明他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第一章的最后,我总结了罗蒂和卡勒对艾柯的批判,从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角度指出了艾柯理论的局限性。第二部分试图在文化研究的理论语境中重新阐释这个问题,因为文化研究的受众研究共享同样的元理论、符号学,至少在霍尔的《编码与解码》中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与艾柯进行对话是合适的,这意味着艾柯的理论不能解决意识形态文本的问题,甚至可能再现一个没有抵抗力的读者,这将再现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模范读者。然后,我借用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的理论模型,提出了我自己的解决方案,试图解决这个意识形态的后果。
1
艾柯解释理论当中的读者角色
关于解释的文学出现在艾柯学术生涯的早期和中期阶段,这可以算作是艾柯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问题。他通过《读者的角色》(1979年)、《玫瑰之名》(1983年)、《符号学与语言哲学》(1986年)、《阐释的界限》(1990年)和《阐释与过度阐释》(1992年)等作品发展了一套阐释理论,并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后结构主义进行了对话。他之所以过分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误读了后结构主义皮尔斯的符号学,特别是德里达和耶鲁解构主义学派,他们在文学批评的学术圈里提倡对漂移能指的无限解释,这使得他在无限符号化的后果上非常恼人。在这一部分,我将布置这一理论背景,将阐释的争论置于语境之中,同时重建艾柯的阐释理论,包括罗蒂和卡勒的批判性回应。
1.1 讨论的背景
艾柯指出了当代符号学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在六十年代,符号学研究的是结构、系统、代码、范式、语义场和抽象对立。它关心的是千年传统赋予它的对象: 符号或符号功能。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符号的识别和定义。第二阶段: 七十年代出现了从符号到文本的剧烈转换,文本被认为是由文本语法产生的句法语义结构。新的问题是文本的承认和生成。第三阶段: 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语篇理论向语用学的方向发展,最新的问题不是语篇的生成,而是语篇的阅读。然而,阅读不再是指批判性的解释或者或多或少的精炼的解释学问题; 相反,它关注的是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认识到读者的反应是文本策略中的一种可能性。(1981,《符号理论与读者角色》)
艾柯概述了符号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符号到文本,从文本到读者。然而,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以及发生了哪些潜在的理论风险。因此,在本节中,我将非常简要地介绍这一理论背景。
在我看来,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其中转折点是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是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模型,二元对立系统的能指与所指, 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 ,这有一个巨大的影响结构主义思想家,如拉康(1901-81年) ,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年) ,巴特斯(1915-80年) ,阿尔都塞(1918-90年)。然而,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总是强调结构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换句话说,僵化的结构主义体系使他们陷入这种静态的思维方式,无法在其中找到行动者的可能性。然而,一旦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被接受,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克服索绪尔的束缚。
皮尔斯提供了一个三元模型,对象-代表-解释器,包括真实的对象在世界和解释器的智力能力。因此,理论家能够探讨的能力,解释员是一个符号系统,对应的第三阶段的符号学在艾柯的分析。然而,皮尔斯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这个符号学体系是无限的,即无限的符号分裂,因此“在这些符号流中,解释、赋予总是随时准备回归到解释的动态,成为其他符号的对象”(2015,Lorssuo)。因此,德里达借用皮尔斯的无限的符号解构了先验所指,或者换句话说,基础主义。在《论文字学》一书中,他写道:
皮尔士在我所说的超验意义的解构方向上走得很远,这种解构在某个时候,会给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参考带来一个令人安心的结局。我已经确定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存在的形而上学是对这样一个所指的迫切的、强大的、系统的和不可抑制的渴望。现在,皮尔士认为参照的不确定性作为标准,允许我们认识到,我们确实是在处理一个符号系统。是什么刺痛了意义的运动,是什么使它不可能被打断。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征兆。(1976: 49)
因为皮尔斯,德里达能够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即超验的所指。然而,正如艾柯所坚持的,它开启了一个解释的危险后果: 由于无限的符号分裂,对文本的解释可以是无限的,这意味着符号分裂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虽然艾柯承认文本的开放性,但他仍然希望建立一个标准来告诉译员在哪里停止。否则,解构主义者的解释只是另一种类型的神秘主义(1992,艾柯)。这就是解释的有效性问题。
1.2 艾柯的诠释理论
艾柯对皮尔斯在后结构主义的误读非常不满意,他想给出一个解释理论,找出一个无限次的符号分裂可以停止的点。在《诠释与过度诠释》(1992)的前两个讲座中,他提出了对后结构主义的历史批判,揭示了它们只是封闭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复发。在第三节课中,他给了我们一些基本原则,以便找到解释的局限性:
(1) 经济原则
(2)语篇的连贯性
(3)模范读者
(4)主体间协议
第一原则(经济原则)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与奥卡姆的剃刀 novacula Occami (“没有必要,实体不应该成倍增加”)有着相同的逻辑。这意味着,当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最好的答案应该总是最简单的。同样,艾柯希望利用经济原则来排除那些非常多余或复杂的解释。事实上,这个原则也是溯因推理 · 普莱斯在《经济、金钱、时间、思想和能源的经济问题》(CP 5.600)中的实用主义的核心指导原则。现在,我们知道皮尔斯已经想好了在哪里停止无限次的信号分裂。根据经济和溯因推理的逻辑,皮尔斯完成代表人和解释人之间的递归是可能的。
第二个原则是语篇的连贯性。艾柯坚持认为,在作出解释之后,应遵循案文的意图,即解释应包括案文的其他部分,以便作出良好的解释。艾柯承认读者可以自由地阅读文本,使用文本,而对文本的解释应当与他所建议的文本一起引导,即”即使不能就文本所鼓励的含义达成一致,至少对于那些不利于文本的含义也是可能的”(1990:45)。要证明文本意图的一致性,唯一的方法是”将文本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加以检查”和”内部的文本连贯性控制着读者在其他方面无法控制的动力”(1992:65)。从而,艾柯重新确立了理解视域的解释学思想。
模范读者在他的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记得符号学的第三个阶段,文本的阅读,那么读者的角色总是在焦点上。艾柯认为模范读者是文本策略的产物:
读者的主动性基本上是对文本意图的推测。文本是为了产生模范读者而设计的一种装置。我再说一遍,这位读者不是唯一做出“唯一正确”推测的人。文本可以预见一个模型读者有权尝试无限的猜想。(1992: 64)
然后,模范读者可以对文本的意图进行推测,遵循文本的连贯性,限制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范围。这就是艾柯区分文本的使用和对文本的解释的原因,即文本的使用不一定是对文本的猜测,而对文本的解释必须是猜测。
他的理论的最后一个限制是,解释也需要在读者群体中有一个主体间的一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非直觉的,非天真的现实的,而是推测的,真理的概念的主体间保证”(1990:39)。这样,我可以说艾柯持有一个认识论的解释集体主义观点,以帮助读者证明解释的合法化。
基于解释的四个原则,艾柯相信他能够找到一个解释文本的守护者。然而,我不认为他能成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我对文化研究背景的评论。首先,我认为有必要谈谈罗蒂和卡勒的反应。
1.2.1罗蒂和卡勒的反应
在《阐释与过度阐释》的后一章中,罗蒂和卡勒对艾柯的立场作出了回应或批判,对阐释持有不同的立场。
罗蒂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文本的”使用”和文本的解释,因为文本的连贯性仅仅是一种解释性假设,它是基于译者对文本的假设,或者换句话说,文本连贯性的辩护只能依赖于解释者的循环论证。罗蒂认为,区分“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1992:106)使用文本更为恰当。只要它对我有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捍卫者,Culler 认为 Eco 的解释理论可能过于保守。用过度解释这个词来思考这个问题有点误导人,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解释,因为我们不应该吃得太多。然而,在阅读文本时却并非如此,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们对文本进行过度的解读,而不是过度的解读,会对文本产生新的理解
他建议我们可以使用“过分”一词(1992:114) ,而不是过分解释。他表示:
理解就是提出问题并找到课文所坚持的答案。[ ... ... ]相比之下,过分强调包括追求文本不会向其模范读者提出的问题。相对于艾柯的观点,布斯的反对意见的一个优势在于,与这种被有倾向性地称为过度解读的做法相比,它更容易让人看到过度解读的作用和重要性。正如 booth 所认识到的那样,提出文本中不鼓励提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成效的。(1992; 114)
卡勒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思考解释,而不是艾柯的模范读者。读者或翻译者从文本中提出问题,而文本的意图并不能说明问题,这一直是读者或翻译者的职责。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由于生成语境的限制,他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模范读者,因此这并不是对解释的限制。卡勒的这一立场非常接近阿冈本意义上的“当代”概念。我将在下一节详细说明。
总的来说,罗蒂和卡勒都认为艾柯在诠释理论中捍卫自己的立场方面做得很糟糕。我将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艾柯进行评论,因为文化研究也有一场关于受众角色的辩论,我认为这场辩论与阐释问题和读者角色有着相同的元理论上的联系。
2
文化研究里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出现了受众转向现象。我将简要地向听众陈述这场辩论,并与艾柯进行对话,以展示他的模型读者概念的纲领性,以及限制互操作的意识形态后果。
一般来说,文化研究对受众的态度有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两种。在《启蒙辩证法》(1944) ,Adorno 和 Horkheimer 认为观众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角色,他们只能接受文化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样,阿尔都塞在他著名的研讨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不是压制性国家机器的机制进行的,因此主体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中,属于一个被动的机构。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葛兰西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协商的霸权观念的影响,霍尔和他的继任者菲斯克认为观众在接触或消费文化产品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发现受众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同时表现出抵制和挪用。因此,霍尔在《编码与解码》(1973)中将受众分为三种类型: 主导、协商、对立,呈现出受众与文化的三种不同关系。霍尔在这一阶段的理论语境是符号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诠释的问题和观众的角色联系在一个元理论层面上。
根据艾柯的解释理论,文本的意图通常会产生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有时会产生一个协商的读者,但绝不会产生一种对立的代码。因此,意识形态的后果往往是受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顺从产物,这在文化研究中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我倾向于成为一个对立的读者,去询问和发现文本的意图并不想让我知道的东西。阿甘本(2008)把这种类型的人称为“当代人” ,他们能够与自己的年代保持距离,能够在光明中找到黑暗,能够凝视自己的时代。我认为一个好的读者 / 读者 / 解释者应该具有与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相似的当代美德,去解读文本的黑暗,保持距离,凝视文本,发现文本的荒谬就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 ,发现文本中的光的缺失就是阿尔都赛的双重性。
也许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光的隐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光总是被认为是积极的、先进的、开明的、理性的、充满希望的。然而,如果这道光被灌输了意识形态,我们该怎么办呢?毫不奇怪,我们知道柏拉图用光来比喻他的“理念” ,而洞穴里的人只能看到墙上的阴影。现在,艾柯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文本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意识形态,我们怎样才能相信文本的意图,成为一个模范读者呢?如果我们设定一个解释的极限,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出洞穴,或者,在最强烈的情况下,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真实与非真实之间没有区别)。
我认为艾柯并没有一个基于他的解释理论的答案。
2.1 解决方案: 读者的相对自主权
我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文本和解释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文本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能够将解释视为文本的实践。然而,在文化研究中,经济还原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被拒绝,而更新版的基础-上层建筑,多元决定论,赋予上层建筑相对的自主权,在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1970)、《读资本论》(1965)、《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1)和《弗洛伊德与拉康》(1971)中重新阐述了基础与结构的关系。他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38)中的多元决定的概念,指出了不同实践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理解文本与阐释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也存在着多重冲击。
我把它放在下面,关系文本——解释在其实践中构成多种力量,在这些力量中,解释被矛盾的力量所决定,读者在最后的意义上有一个功能来决定什么是对他最好的解释。正如巴特区分一介秩序作为能指的外延,二介秩序作为能指的内涵,它与文化、知识、历史有着密切的交流,可以说,正是通过它们,环境世界侵入了语言和语义系统。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意识形态的碎片”(1972,《神话学》)。他对二阶能指的理解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模型,从而可以概括出文本解读关系中的力量: 模型作者、经验作者、文本意图、经验读者、模型读者、文化、历史、读者知识、社会知识、意识形态、审查制度。这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
本文认为解释的相对自主性是对艾柯的一种回应,由于解释的实践不能被视为与其他实践的孤立,所以它不仅仅是由文本决定的,同时又坚持读者的重要性,因为即使读者是嵌入在复制领域中的,解释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由他自己的文学实践决定的。这种模式承认解释的开放性和对读者进行的动态斗争的辩证法。
在我的模式中,读者在文本中对霸权意识形态持有反对立场,他可以发现文本的症状。我把对文本的解读看作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阶级冲突或权力关系。在实践的最后,这位对立的读者能够抵制意识形态,或许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它适当地运用到自己的解释中。此外,这种解决方案是兼容位置罗蒂和卡勒。这种解读取决于一个人的实际目的,也为读者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解。
结论
总之,本文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本阐释的经典论争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是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尤其是阿尔都塞与艾柯之间的一次成功对话。在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是理论讨论的中心话题,而艾柯的理论中却没有意识形态。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艾柯的模范读者,他的模范读者包含着可以被整合进意识形态的潜能,但是他却无能为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结构范式,我可以重新思考文本与阐释的关系。我深受阿尔都塞的启发,他用过度决定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基础-上层建筑。因此,我可以给读者一个相对自主的解释实践,以解决意识形态文本的问题。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概念对我思考读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也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W., and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2016.
Agamben, Giorgio.“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thusser, Louis.For Marx.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9.
Althusser, Louis.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Verso, 2014.
Althusser, Louis.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1997.
Barthes, Roland.Mythologies. New York, NY: Hill and Wang, 2013.
Derrida, Jacques.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Eco, Umberto, and Stefan Collini.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co, Umberto. “The Theory of Signs and the Role of the Reader.”The Bulletin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4, no. 1 (1981): 35. https://doi.org/10.2307/1314865.
Eco, Umberto.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Eco, Umberto.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Eco, Umberto.The Name of the R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83.
Eco, Umberto.The Role of the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Freud, Sigmund, and Abraham Arden. Brill.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Kant, Immanuel.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ndianapolis, Ind.; Cambridge: Hackett, 1996.
Lorusso, Anna Maria.Cultural Semiotics: for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Semiotic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Saussure, Ferdinand 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