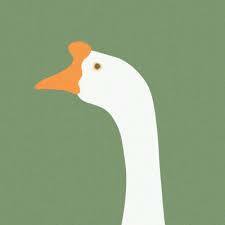信仰、真相与人性的对峙 ——芥川龙之介的怀疑之眼
(本文为读书小组活动笔记,所以含两篇文章的书评,无关内容请包涵~)
《南京的基督》与《竹林中》都是芥川龙之介中晚期的作品。两篇故事各有特点和侧重,但共同反映了芥川这一时期鲜明的的怀疑主义思想。具体来说,芥川认为宗教信仰和客观真相这样看似宏大、确切、不可动摇的存在可以被人的心理严重扭曲和利用,而最终导致信仰可能失去其崇高的地位和约束力,真相也变得无从得知。
(以下含剧透)
《南京的基督》里,金花被塑造为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有一种理解是金花的病在与无赖嫖客过夜之后确实痊愈了,金花因其虔诚和善良之心得到了救赎 ,而嫖客则因欺骗金花遭受了报应暴毙而亡。因为小说是开放式结局,这种理解有成立的空间,但考虑到芥川一贯的讽刺手法以及对描绘人物复杂心理的追求,我倾向于另一种内容更为丰富的解读,即并非信仰救赎了人,而是人利用信仰释放了内心。
金花的信仰在一开始就通过日本恩客之口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金花无疑是相信上帝及其救赎的存在的,但是金花对于基督教义的理解明显地迎合了她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需求,虽然圣经中也有妓女凭信仰得到救赎的故事,但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理解基督教义的人会自然地将基督与底层官差作比较,或是心安理得地为妓。金花对信仰的理解并不是通过约束和改造自己换取救赎,而是上帝会无条件地理解和原谅自己的过失。于是金花在患病之后虽然有意识地拒绝客人以免他们患病,但这种决心在生活的压力下又无法做到十分坚定。这种矛盾的心情在无赖嫖客到来并提出给她十美金巨款的时候达到了巅峰。此时在故事中信仰第一次充当了金花合理化自己行为的工具,金花相信了嫖客是基督的化身,基督必定是为她而来,而且也是不可能患病的,于是两难的处境迎刃而解。金花安心甚至是幸福地与嫖客发生了关系,并在梦中完美地实现了自己被救赎的愿望。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略微清醒的金花再次陷入了由良心的谴责、一时忘情的羞耻、以及金钱损失的懊恼等复杂心情带来的折磨。此时信仰第二次给了金花化解矛盾的理由——金花发现梅毒症状消失了,于是对嫖客就是基督并治愈了自己这个解释深信不疑。金花完全无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她的症状消失是因为把病过给了客人。这种无视究竟是有意无意似乎也没有区别,因为金花有“信仰”这一强大的武器,可以在她自己的逻辑内合理化一切对她的道德感和自尊造成威胁的行为。金花面对日本旅行家的质疑,坦然宣称自己已经痊愈。至此,信仰原本的规劝意义已经丧失,反而被金花所利用来维护“自我”的和谐完整。
虽然芥川看似深刻地批判甚至讽刺了金花,但他埋下的一条暗线其实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信仰本身。嫖客并非基督,梅毒也不可能靠过给别人治愈,金花的病更有可能是进入了潜伏期并将会更凶险地发作,但金花在幻想中获得了更甚于很多正统教徒的莫大的幸福。芥川停笔于此,使“暴风雨前的宁静”带来的反差和不安达到最强,从而传达他对信仰意义的怀疑。金花的故事呼应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章关于信仰的反思:自由的信仰是否比幸福的保证更值得追求。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思更多是对于信仰失去影响力的不安,而芥川则怀疑信仰的救赎是否比金花幻想的幸福更有价值。
《竹林中》所呈现的困境和怀疑对于没有成长在宗教信仰文化下的读者来说可能更为普适。这篇小说完全没有采取外部叙述者的视角,而是让事件的不同参与者各自讲述了一遍事情经过,呈现的效果就是远离事件的旁观者无法提供信息,处于事件核心的三人的叙述则大相径庭——每个人都把事实按照自己的愿望扭曲了。
在盗贼的故事中,他主动承认自己杀害了武士,但将过程描述为应武士妻子要求与武士进行了公平的决斗并战胜了武士。武士妻子也声称是自己杀害了丈夫,并将原因归结为丈夫的嫌恶鄙视。武士本人(的鬼魂)则声称自己是对妻子的背叛感到绝望于是自杀。仅凭三人的叙述很难还原故事的真相,但与真相之扑朔迷离形成反差的是三人各自心理活动的昭然若揭。盗贼希望维护自己敢作敢当、武功高强的形象,武士妻子要表明自己宁死也不肯接受丈夫羞辱和抛弃的刚烈,武士则要以自戕来洗刷被妻子背叛的耻辱。芥川在此提出的第一层怀疑就是,每个人都有扭曲事实的动机,那么我们每天通过他人接受的无数信息,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而背后的事实又是否可能被还原。
再进一步考虑,这个故事的直接矛盾在于被有意识的谎言掩盖的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毕竟是唯一存在并可能被更先进的技术还原的。然而就算还原了客观事实,“真相”也依然可能无从确认。根据认知心理学,同样的客观事实,在不同人的认知加工下可能产生迥异的解释,而事后对于事实的回忆又会被每个人的既存信念和情绪所改造,于是“真相”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根本就是不同的。譬如故事中的三人都提到了武士妻子受辱后的叫嚷,但是盗贼将其解释为煽动争斗,武士将其解释为背叛灭口,而武士妻子自己的解释更像极端恐惧绝望下的情绪宣泄。我们既无法确切得知武士妻子的话语,也无法推断杀意究竟来自谁的“主观故意”。于是我们可以导出的第二层怀疑是,如果对同一事实的解释不唯一,那么“真相”又是否唯一存在,追寻真相的意义为何。
《竹林中》隐喻了现实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困境。在面对很多人际纠葛或社会冲突时,我们总希望先“还原事实真相”再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同样秉持这一原则的人们依然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如果真相既不可得,又无法指导人们的认知和判断,那么真相的意义何在?
《竹林中》是芥川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后被黑泽明翻拍为《罗生门》。《南京的基督》则是芥川涉及宗教思考的代表作。芥川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复杂心理把握极为精准,无论是他早期较强的批判性,还是晚期的超脱幻灭,都通过笔下人物或癫狂或滑稽或温情的言行表现得巧妙又清晰。虽然芥川的叙述常常带有对人性顽劣之处的讽刺调侃,但是因其对人复杂心理的深刻理解和高超描绘,这种讽刺并非居高临下的鄙夷,而是对于善恶的一体两面性的思考,以及对于纯粹的真善美究竟是否可得的疑问。事实上,芥川往往在讽刺背后表露的是对自相矛盾的人类的极大关怀和包容。但这种包容之心没能战胜作家内心对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一贯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虚无感与绝望,致其于35岁便自杀身亡。芥川的写作格局超出了绝大部分日本作家,文风也是独树一帜的简洁直白,以其名设立的芥川奖一直是日本文坛纯文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
推荐拓展阅读:《罗生门》、《地狱变》、《蜘蛛的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