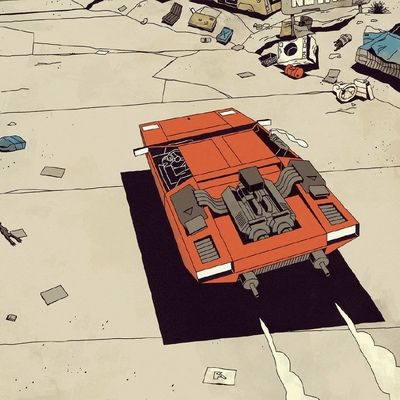每个读过的人都会有话想说
对读者来说最痛苦的事就是理解了这本书。如果在读完后感叹文学巧言令色,香消玉殒,着眼于文字的精美,或是质问为什么,怎么办,都是没能理解。活着的人才会问怎么办。没见过的人才会问如果该怎么办。破碎的人只能是破的,再有才华,也就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如何的破,甚至能把破的地方指给人看,但是碎了就是碎了,她没有选择,从那一刻开始她永远都是人生的赝品。谈没有,谈其实可以,都是理解破碎的无能。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受苦经历,遭受过暴力的人,不一定要是女孩,都可以理解其中的痛苦经验。痛苦的经验可以分享,痛苦不行。痛苦是无法被理解的。比如作为小说的不成熟,除了有些地方过于工笔,还有把老师写成了扁平的邪恶。恶是没办法被理解的,房思琪当然不理解老师,她一直都在表达对老师的轻蔑。轻蔑在小说里很容易失败。我做过恶人,恶人不会想今天我要计划作恶。恶人会有成功的喜悦,失败的苦恼,遗世独立的骄傲,恶人会想这会儿最好躲一阵风头,换个地方继续活下去。要让恶人理解自己是恶人,可能比让受害者理解自己受害更难,因为受害者可以把自己的受害经验传给小群体,但恶人是封闭的,恶人是被遗弃的孤儿(没有同情之意),恶人可以学习成为恶人,但是恶人之间没有经验传递。房思琪不能理解老师。老师是她辗转难眠的夜晚里沉默无言的黑暗,她知道黑暗里自己的痛苦,她不知道那黑暗是什么。
但是我们不应该试着去理解恶。我拒绝理解。我拒绝听老师悲惨的姐姐上吊的起源故事。恶人才应该去理解受害者的痛苦。房思琪一直在试图去理解老师,不能理解也要去爱,我相信她认为自己是真的爱上了老师,那时她真的会感到快乐,如果不理解那就是还不够爱,所以她要继续去爱,哪怕知道老师骗了她,但是没有关系,如果老师需要,她就要把自己所有所有的全都拿出来,把他填满,这样才是爱。她道歉,因为她做的不够好。我觉得每一个对语言有所期待,对文学有所期待的人,都能理解女孩的幻灭。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很多,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你发现原来只是一个骗局,你怎么办。她花了一个人生去认识到不是自己的错,最后她还是碎了。你不是她,你是还活着的那一个,你怎么办。你不能拿怎么办这种问题去问她,问老师,问她的书,问别人。怎么办是一个轻蔑的问题,轻贱了她的痛苦。破碎就是破损,痛苦就是痛苦。她非常聪明,也有才华,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对读者的期待是,如果看完本书觉得还会有希望,那么就是还没能理解。痛苦和希望毫不沾边,痛苦就是没有希望。和梦幻,美,书写,存活都无关,只和痛苦有关。
如果真的有所谓希望这样的东西,那会是什么?我不是房思琪。你也不是房思琪。她是疯了的,死了的,她不是那活着的人,因此活着的人不是房思琪。清明节应当祭奠。读者没有经历过同样的痛苦,但通过她仍然看到了世界的背面,无论是否理解,但你知道了背面的存在,这就是替她而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