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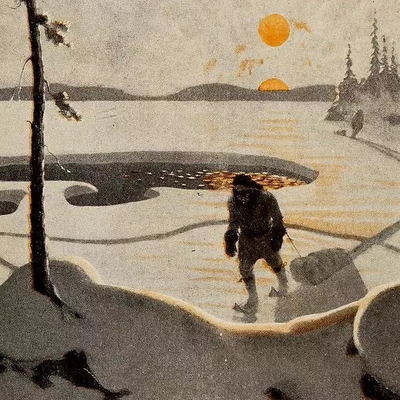
副标题是“为明天而行动的方法”, 一本立场鲜明的书籍, 环保主义者的工具。这本书介绍了Gilles Clement(景观设计师,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是从园丁的角度出发去工作,但又比普通园丁有着更宽广的视野)与Philippe Rahm(建筑设计师)对环境问题各自做出的回应与策略。简单来说,Clement谈如何以最少的手段干预自然环境,挑选一些可能的场地去重构其生态多样性,这些地方统称“第三景观”,包括1城市零碎空间与各种废弃地、2未经开发的原始自然、3人工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其中1最值得深入研究。 Rahm谈如何以科技手法设计最宜居且最节能的生存环境,认为从气候出发来测算并推导建筑的形式与功能才是人类的未来。
两人都对人类的文化活动与社会身份不感兴趣,眼界放在自然问题这一当务之急上。Clement挑选去设计的场地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没有涉足或者被人类文化抛弃了的地方,它们本身就有着无身份无场所的特性。他说自己尽量不提“生态”一词,因为不想与政治上的环保主义扯上关系,我倒是欣赏。Rahm的理论我只是速读,看豆瓣有人说他的决策并非真的基于测算,那么看来他只是试图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陈述一种方法论而已。他似乎不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是,纯粹以各地不同气候出发所设计出来的建筑,最后有没有可能在某个角度形成当地的独特形式?气候本就与人类的饮食居住及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而直接通过测算推导出来的“最佳形式”,最后会在什么地方与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生联系吗?我猜答案仍旧是否定的,这样想来,建筑学原本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学科,而今人文的越人文(或者艺术的越艺术),自然的越自然,毕竟大家都赶时间,哪有功夫两头都顾。文化向左,文明向右,艺术终究是人类文化的高光,而人类正在毁灭自然,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们的文化?
文化传统太容易沦为假大空的说辞——但并不是说它们不重要。可悲的是,人类群体终究是需要文化身份的生物——也正因为是这样,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胡编乱造也容易销售。所以对文化传统产生真正透彻的理解并在这之上进行建造是极其困难且短时间内未必讨好的事情。
两人的设计都直接从场地的物理生物属性出发,高度文明的曙光,科学理性的未来。终归是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大浪淘沙的两朵浪花。Clement的手法亲民造价低廉,但他并算不得一位景观设计师,是一位走入分支的学科研究者。不知道Rahm建造一栋建筑的造价,想来成本无法降低,而无法普及的手法又如何可能成为人类的未来呢。
所以上周副导问我:你是在为人类做设计还是为自然做设计?真是一个极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