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与平等 —— 论朗西埃美学中的平等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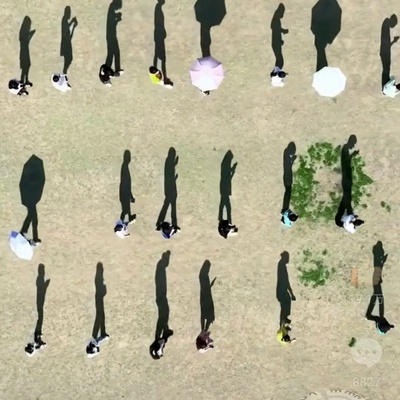
Quote
“To explain something to someone is first of all to show him he cannot understand it by himself.”Jacques Rancière, 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正文
- 引言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中心主题。许多像阿尔托和布莱希特这样的戏剧思想家认为,戏剧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荒谬,从而重建一个政治能动者。的确,这种解放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很容易找到。在马克思、布迪厄和阿尔都塞看来,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形成了一种虚假的意识。那么,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帮助无产阶级接受理论工具的训练和装备,以便根除这种意识形态。然而,对于一个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雅克·朗西埃来说,这种解放的逻辑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不平等的公理。他不同意进步主义的解放逻辑,因为它将平等置于未来。然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解放逻辑,即预先假定平等的公理,当我们行动时,主体就会被解放。本文将从《无知的大师》(1991)、《被解放的观众》(2009)和《美学政治学》(2013)三个方面重构他的平等理论,从教育学的秩序、旁观者的秩序和美学的秩序三个方面来评价他的平等理论。在本文中,我将从三个角度(教育学、戏剧学和美学)论述这三种相互关联的秩序可以作为他的平等哲学的基础。
在本文中有三个主要部分,我将分别讨论它们,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一个连接。第一部分介绍了他对教育学的贡献。我把他的方法概括为无知的辩证法。这种无知的辩证法体现了无知大师的智慧和当前教育学中的逻辑矛盾。他提出以平等公理而不是不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知识解放,给予具有与老师同等获得知识能力的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接下来的部分扩展了他在第一部分的论点,并应用于戏剧主题。他反对以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前提的戏剧解放的流行思想。他不同意消极观众的观点,但他坚持认为观众是积极的行为者,把观众看作演员的对立面是错误的。第三部分是他论证的核心,讨论了他与美学相关的两个术语: 感性的分配和艺术体制。这两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平等理论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是建立在我们的“共同感”之上的。最后,为了清晰起见,我以分析哲学的形式重构了他的论点。然后,最后一部分对他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我将试图为他辩护。
- 教育的秩序
在这一部分,我将根朗西埃的著作《无知的大师》(1991年)和一篇短文《论无知的大师》(2010年) ,重构他关于教育秩序的论证。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约瑟夫 · 雅各托特的故事,他在19世纪20年代左右,在鲁汶教他的学生法语,但他对法语一无所知。他给了他的学生一本双语版的Telemaque,要求他们通过这本书的翻译来自己学习法语。一个学期过后,他所有的学生都能说很好的法语,而他什么也没教他们。然后,他还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来教授他的学生其他他也不知道的学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他发现了“无知的美德”(2010年) ,这意味着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新逻辑。
在传统的教育秩序中,教师从教科书向学生传递和解释知识,呈现出一种不平等、无知学生与有知识的教师之间不平等的秩序。这一观点受到了雅各托和朗西埃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教学关系中,学生的无知每次都被重新证实,知识与学生的距离总是被教师重新创造出来的。这就是雅各托所说的“愚蠢化”。
朗西埃希望重塑这种有问题的教育学秩序。他(2010)指出无知的美德有三个层次:
经验水平。基于教授学生法语的过程,雅各托得出结论,“一个无知的人可能会允许另一个无知的人学习双方都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层。“教书的老师——也就是道路上的老师——不传授任何知识。” 因此,掌握知识和教师的知识之间的联系是分离的。
第三层次: 大师对“不平等的知识”一无所知。
这三个层次的无知表明了无知美德的内在逻辑。对于一个无知的教师来说,不是什么都不懂,随心所欲地教导学生的人。无知美德的偶然发现实际上是对现有教育逻辑的挑战。一般来说,无知的美德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智力去学习任何东西,并且没有必要有教师这样的媒介来教授 / 传播 / 解释知识给他们。
我把无知的美德称为无知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原则上,没有人能够阻止另一个人获得知识,即使他们都不知道知识。然而,只有拥有知识的人,如知识渊博的教师,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或她成为知识与学生之间的知识阐释者,阐释的过程可能是无限的。朗西埃(2009)解释说: “要用知识取代无知,他必须总是领先一步,在学生和他自己之间安装一种新的无知形式。” 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这是我们现行教育制度中教育学秩序的共同假设。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那些意识到自己没有学习能力从而停止学习的学生变得愚蠢。
第二层次的无知告诉我们,教师没有必要把知识从他们的头脑传递给学生。学生能够运用他们共有的智慧自己获得知识。值得注意的是,朗西埃哲学的主要基础是智力平等。朗西埃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智力,因为他们能够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会自己的第一语言。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学校,孩子们就会被教育的不平等秩序所愚弄。无知的大师的智慧在于他或她对不平等的知识一无所知。从而创造了教育学的平等秩序。朗西埃 (2010)提出“这个逻辑,在平等的前提下运作,并要求它的验证,这个逻辑值得称为‘智力解放’”。这种智力的解放是智力平等的证明。无知的大师的任务是根据在符号森林中的随机遭遇来验证他们所看到、发现和学习的东西。
教育的秩序就是社会秩序。对朗西埃来说,解放的第一步不是教无产阶级哲学或革命理论,而是告诉他们有学习、阅读和思考的能力。这就是他所说的“智力解放”。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通过雅各托的故事,而且是基于他多年来对法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劳动之夜》 ,1989) ,他发现工人阶级能够从事哲学、诗歌和文学,而他们的语言更加清晰和简洁。
但是无知的美德是如何与艺术和政治相结合的呢?这是我将在下面几节中回答的问题。
- 剧场的秩序
这一部分的目的将集中在朗西埃的戏剧理论上,该理论基于《被解放的观众》 ,这本书将他的论点从教育学的逻辑发展到戏剧的逻辑,他发现,在这个地方,演员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不平等的关系。对他来说,在教育学和戏剧之间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因为这两者都预先假定了一个类似于社会秩序的不平衡的概念。
一开始,他指出了戏剧史上观众的悖论,暗示了“观众是一件坏事”的观点。这是戏剧讨论中的一个常见假设,它导致我们需要“一个没有观众的戏剧”这样一个结论。其逻辑是,观看总是被视为与知相对立,也与表演相对,因为与积极参与戏剧制作和表演的演员和剧作家相比,观众是一个坐在那里观看戏剧的被动能动者。因此,这种观众被动的观点得出两个结论: (1)剧场绝对是一件坏事; (2)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剧场(一个没有观众的戏剧)。
前者可以在柏拉图的艺术批判中找到,柏拉图认为“戏剧是一个让无知者看到人们受苦受难的地方” ,而后者则出现在现代戏剧理论中,如布莱希特和阿尔托。朗西埃的讨论仍然停留在第二个结论上,这是批评家中最流行的结论:
根据他们的说法,谁说“剧院” ,谁就说“观众”——这就是邪恶所在。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戏剧圈子,正如我们的社会已经按照它的形象塑造了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剧院,一个没有观众的剧院: 不是一个在空座位前面演出的剧院,而是一个剧院,其中被动的光学关系暗示着他们是受制于一个不同的关系-这是另一个词所暗示的,这个词指的是在国家戏剧中产生的东西。戏剧意味着动作。剧场是一个地方,一个行动是采取的行动,在运动的身体前面的活体将被动员(2009年3月)。
这种对新剧院的推广主要是为最现代的评论家所接受的,他们不是要把观众减少到空座位上,而是要把他们的被动转变为主动。这样,观众的身体就会动员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和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剧场有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 “一方面,观众必须被允许有一定的距离; 另一方面,他必须放弃任何距离。一方面,他必须改善他的凝视,而另一方面,他必须放弃观看者的位置”(2009:5)。前者希望创造观众与戏剧之间的距离,形成陌生化对观众的影响,唤醒观众对错误生活状态的认识,后者则希望打破观众面前的“第四道墙” ,使观众融入戏剧。这个逻辑在德波对景观的批判中也得到了延伸。
然而,对于朗西埃来说,这种解放的逻辑和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教育学的逻辑一样,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新戏剧的逻辑假定观众和演员或剧作家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关系,假定一套二元等价和对立关系(2009:7)如下:
等价: 戏剧性的观众与群体,凝视与被动,外在与分离,冥想与拟像。
对立: 集体与个人、形象与生活现实、能动与被动、自主与异化。
他认为,这正是愚蠢化的过程,因为它假定(1)观众和演员或剧作家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关系,(2)智力的高人一等,即剧作家需要通过戏剧向观众讲述一些事情。然而,他认为这种预设是无效的,因为(1)旁观者不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存在,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主体; (2)我们作为观众,并不需要剧作家来解释“社会关系的真相和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2009:11)。他表示:
观众也像学生或学者一样行动。她反对,选择,比较,解释。她把她所看到的和她在其他阶段、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系列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她用面前这首诗的元素创作了自己的诗。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表演——例如,从它应该传递的生命能量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图像,并将这个图像与她阅读、梦想、体验或发明的故事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既是遥远的观众,也是向他们展示的景观的积极阐释者。(2009:13)
他承认观众在观看戏剧时的自主权。虽然这种积极观众的观点可以在许多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中找到(例如德里达) ,这种理论赋予读者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来解释文本,但朗西埃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无知的大师》中的知识解放所发展出来的平等原则,而其他基于皮尔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基于文本的无限符号性。因此,与解构主义思想相比,朗西埃更关心生活在社会中的真实的人。他声称,“当我们挑战观看和表演之间的对立时,解放就开始了; 当我们了解到,构成说、看和做之间关系的不言而喻的事实,属于支配和服从的结构”(2009:13)。他的解放方法可以概括如下:
s(事态)可以改变当且仅当 : 我们头脑中关于 s 的概念已经改变。
这样的认识论断裂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平等是我们行动的前提,而不是目的。只要我们把平等放在行动的假设中,那么解放的时间就开始并成为可能。结构在朗西埃那里成为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可以根据我们的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他首先论述了教育学的秩序,其次论述了戏剧的秩序,以此来问题化不平等的共同基础。
但是,要改变我们对结构的概念,并不那么容易,除非我们重新分配可感物(the sensble),并进入一种新的艺术体制。他补充说,这些对立“定义了感性分配,这些感性的位置、能力和无能力的先验。它们体现了不平等的寓言”(2009:12)。这就是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策略。
- 审美的秩序
感性的分配和艺术体制是朗西埃美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我将阐明这两个概念如何参与我们通往解放和平等的旅程。Citton (2009)指出了解放的观众和感性分配之间的隐含逻辑,即”感性范畴的有用性主要来自于它中和了传统上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对立” 他继续说道:
事物并不只是把它们的形象投射到感官的空白屏幕上: 我们,人类,积极地对它们进行分类。我们过滤它们,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些然后拒绝其他的,我们根据复杂的区分机制对它们进行分类,这些区分机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起来的,每次我们感觉到任何东西时都会进行个体重建。事实上,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敏感性,我们的感知能力,足以表明某种类型的活动,无论它可能是,是参与了这个过程。(2009:121)
“感性的分配”这一术语,是朗西埃对观众重新概念中的逻辑的一种扩展的理解形式,观众不仅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且具有感性的能力,这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康德在他的著作《判断力批判》(1892)中特别讨论了这一“共同感”(common sense),同时这被朗西埃作为提出审美平等论点的基础。
在本节中,我将介绍他关于感性分配和艺术体制的概念,以说明如何能够回答我在上一部分结尾提出的问题。这两个概念主要在《美学政治学》(2013)中进行了论述,该书是将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与美学反思联系起来的重要文本。
根据 Brant 的说法,“对于朗西埃来说,可感的人决定了共同体可以感知到的和共同的东西的不断变化的边界,以及特定的群体对这个空间的要求和表征。因此,基于社会地位及其言论被认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而被纳入或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群体的问题是感性分配的核心”(2018:235)。基于这个定义,朗西埃重新发现,通过“确定他所提出的是艺术和政治表征的共同利害关系” ,政治和美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政治领域决定了言论的合法性,审美领域决定了言论的可见性和可说性。换句话说,朗西埃重新写道: “政治和艺术就像知识的形式一样,构建‘虚构物’ ,也就是说,对符号和图像进行物质重组,看到的和说出的之间的关系,做了什么和可以做什么之间的关系”(2004:39)。政治和美学都创造了包容和排斥被表征权的情况,其中可感物”对共同体及其成员施加了等级制度,同时也规范了他们参与政治和艺术表现”(2018:236)。为了改变这种秩序,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重新分配感性的东西,因为这种感性也是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空间,这就是他的艺术体制所扮演的角色。
朗西埃重新定义了三种艺术体制: 图像的伦理体制、诗学或再现的艺术体制以及审美的艺术体制。事实上,他认为,艺术只能出现在最后两种类型的体制中,因为在图像的伦理体制中,“‘艺术’不是这样被认定的,而是包含在图像的问题中”(2013:16)。必须根据图像的“存在”(或精神气质)及其“道德”的政治后果来考虑形象伦理体制中的“艺术”或形象的产生。这种图像的伦理体制可以在柏拉图的艺术理论中找到,在那里他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当中驱逐出去,以防止他们腐蚀青年。在这种体制下,艺术完全没有自主权。
诗学或再现的艺术体制使艺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制度下的艺术生产并不遵循道德规则,而是遵循现实规则,他称之为“再现性” ,这是通过模仿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社会等级的一种表现。他总结说,”行动优于人物或叙述优于描述的代表性,体裁根据其主题的尊严划分等级,以及说话艺术和言语在现实中的首要地位,所有这些要素都与完全等级化的共同体视野相类似”(2013:17)。前两种类型的体制并不是他理想的艺术体制,而第三种类型的艺术审美体制可以为了平等而改变感性的分配。
审美艺术体制(2013:18)赋予了艺术的完全自主权,因为它根据区分特定于艺术产品的合理模式来确定艺术,而不是通过在做和制作方式上的分工。朗西埃(2013:18-19)指出,艺术的审美体制是“严格区分艺术的独特性并将其从任何特定规则、任何艺术等级、主题和体裁中解放出来的体系” ,并且“断言艺术的绝对独特性,同时破坏任何孤立这种独特性的实用标准” 通过这样做,它创造了“一个分裂的思想和感性的分离从一个无意识的和思想从非思想分离”(2009:231)。换句话说,艺术的审美体制遵循的是艺术的规则,而不是道德的规则(伦理体制)或现实(再现体制) ,同时也表征着不可表征的东西,视觉化了无法被看到的东西,感知了不可感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艺术的审美体制确立了“审美作为一个平等点,或者说是感性与非感性、思维与非思维的同一点”(2009:231)。这个平等点成为他激发审美平等的基础,从而促成后来的政治平等。Vallury (2009)认为,对朗西埃来说,“当一个特定的感性领域被重新分配,当存在、说和做的方式被重新配置,为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出现新的主体化模式腾出空间时,政治就发生了。” 我将他的美学平等论概括如下:
P (1): 每个人都有感觉(共同感)的能力。
P (2): 美学通过确定可见或不可见的东西来定义和界定可感知的领域。
P (3) : 我们的感性可被重新表述,即感性的分配。
P (4) : 感性可以通过艺术体制的改变来重新分配。
P (5) : 如果我们的感性分配是在艺术的审美体制中,平等点就会出现。
P (6) : 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感受(P1)艺术的审美制度。
C (1) : 因此,美学的平等点出现了(感性与非感性、思维与非思维的同一性)。
P (7) : 当一个给定的可感知的领域被重新分配时,政治就发生了。
C (2) : 因此,政治的平等点出现了。
美学平等论是对朗西埃关于感性分配和艺术体制逻辑的简要重构。对他来说,平等点是一个地方,可以改变我们的结构概念,从不平等到平等,基于艺术审美制度中的感性再分配,在可见与不可见、思想与非思想、主动与被动之间产生同一性。
- 讨论与反驳
在前面的三个部分中,我考察了朗西埃哲学中的三种平等秩序: 教育秩序、戏剧秩序和审美秩序。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来坚持人类的本质,即我们在最根本的方面是平等的,这为民主提供了基础。他的主要对话者是柏拉图、阿尔都塞和布迪厄,他们认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制度,无产阶级为了解放首先需要学习这一理论,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通过文化资本进行再生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口味是截然不同的。朗西埃不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假设,而他试图争辩说,工人阶级有同样的能力去感知,去学习,去观察别人。
然而,有一些反对意见可能会提出,我想特别讨论其中的一些。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认识论的,针对的是他关于教育学的第一个论点,即如果像朗西埃重申的那样,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智力学习能力,没有从老师那里传授的知识,那么如何才能确保知识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真实或正确的,因为误解和误读对我们来说很常见,但学生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和内容学习东西。朗西埃可以说,即使我们确保每个人的智力平等,也不意味着武断地学东西。在双方(学生和老师)之间总有第三样东西,那就是书本。如果我们还记得 Jacotot 的故事,他给他的学生一本双语书,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获取书籍或知识,而无知的大师只做验证的工作。在验证过程中,教师会验证他们所看到和发现的符号森林,也就是说,教师只告诉学生如何获得知识,而不是知识是什么。这种回应可以看作是认识论中的程序实在论,即命题 p 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个程序是真的。即使对程序实在论的处理有很多批评,我认为这是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一个充分的回应,因为认识论的问题不是朗西埃在这场争论中的中心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可行性的反对意见,怀疑朗西埃的只思想解放和感性解放能否达到政治上和现实的平等。换句话说,对平等的观念论取经是否能确保为唯物论上的平等?在我看来,朗西埃的哲学既不是是观念论的,也不是唯物论,是两者的结合,是辩证法思想。乍一看,他的论点听起来像是一个观念者,但是如果我们挖掘到底,我们会发现他的主张都是基于对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的经验研究。对他来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非常错误的不平等假设之上的,只要改变这一假设,解放就会到来。因此,他的论点不是一种政治承诺,即如果你遵循他的建议,平等就会到来,而是表明我们社会的逻辑矛盾,告诉我们在解放或革命之前我们需要改变什么。否则,平等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漂移能指。
- 结论
总而言之,我称朗西埃为平等的哲学家。在他的理论中,平等的公理成为第一原则,这也是他想告诉我们的,每个人在最基本的方面(智力、理解力和敏感度)都是平等的。我将他的平等理论重构为教育学秩序、戏剧秩序和美学秩序三个平等的秩序。它们都试图在各自的逻辑预设中表现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美学对他来说既是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手段,也是目的。他告诉我们,为了争取平等,我们必须把平等的原则放在首位,然后再做事情。智力解放始于知识平等得到验证。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的对立也应该消除,这才是分配感性的关键。艺术的审美体制提供了一个平等点,在这个点上美学的平等发生了,同时政治出现了一个给定的领域的感性被重新分配。
参考文献
Bingham, Charles Wayne., and Gert Biesta. Jacques Rancière: Education, Truth, Emancip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0.
Bray, Patrick M.Understanding Rancière, Understanding Modernis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Brant Daniel.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In Understanding Rancière, Understanding Modernism. Bray, Patrick M.235-238.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Cittton Yves. “Political Agency and Ambivalence of the Sensible.” In Jacques Rancière: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 Rockhill, Gabriel, and Philip Watts. 120-13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ancière Jacques, Donald Reid, and John Drury.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89.
Rancière Jacques.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Translated by Kristin Ro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Rancière Jacques.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London: Verso, 2009.
Rancière Jacques, “On Ignorant schoolmasters.” In Jacques Rancière: Education, Truth, Emancipation. Bingham, Charles Wayne., and Gert Biesta,1-24. London: Continuum, 2010.
Rancière Jacques, and Gabriel Rockhill.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Rockhill, Gabriel, and Philip Watts.Jacques Rancière: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allury Raji. “Politiczing Arts in Rancière and Deleuze: The Case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Jacques Rancière: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 Rockhill, Gabriel, and Philip Watts. 229-14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诡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