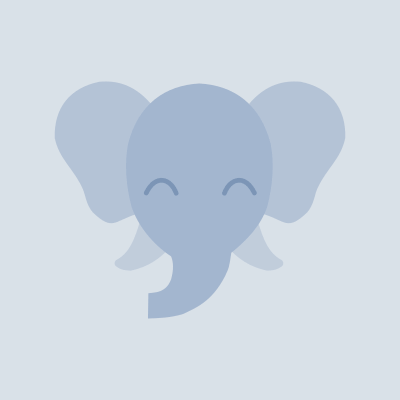听不见的声音
还在做记者的时候,经常和别人探讨社会新闻记者写的关于杀人案的报道。人们总是会问,为什么要去追究嫌疑人的身世。记者们的辩护通常是,需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犯罪,才能从体制上去解决造成犯罪的问题,从而制止新的犯罪产生。这种说法冠冕堂皇,但是归根到底,它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如何知道经由记者重述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
观众看到了亚瑟·弗莱克的苦难。他生活在一座毫无希望的城市当中,作为一名小丑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母亲病重即将离世。精英们高高在上,以一种施舍的态度面对底层的人民。亚瑟还有心理疾病,而为他服务的社工项目因为政府财政紧缩而被取消。当打击连番而来的时候,他最终被逼着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为了罪犯,成为了整个城市暴动的象征物。
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它只关注到了亚瑟所处的环境。观众能够理解亚瑟愤怒的理由,他被歧视、被践踏、被毫不在意地像垃圾一般对待。但愤怒是如何变成一种杀戮的行为?在选择将枪指向羞辱他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很希望电影在这个层面上给我更多的答案。仅仅将整个因果链条归咎于,“我遭到了羞辱,我难以忍受,因此我要杀人”,就会变成一个极其简单的条件反射性的回答,而人的主体性,以及主体性带来的道德性,就会因此被全部抹杀。也就是说,当亚瑟被刻画得越是悲惨,亚瑟本身就越成为了一种动物,电影本身对于亚瑟的全部刻画,就会沦为一种自然的兽性逻辑。亚瑟因此成为了一个符号,代表着体制性崩溃的受害者,而他真正的主体性并不会被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小丑》展现出来的亚瑟与影片中精英对于亚瑟的质问成为了一种互相照应,如同影片中的精英所说,“我能够拯救你们,只要我们对于我们的体制作出一些变化”。
人真正的主体性存在于选择的瞬间以及其背后的逻辑,来自于权衡以及思考。在展现主体性的角度,做的更好的影片是《大象席地而坐》。两部影片可以类比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都展现了一个沉闷社会对于个体的压迫。但相比起《小丑》中,亚瑟作为一个纯粹受害者的角色,《大象席地而坐》中展现了更多主角的能动性。彭昱畅饰演的韦布为了帮助同学而四处游走。李从喜饰演的大爷会因为自家被别家咬死的狗而上门质问。章宇饰演的于城则最为充分,他所做的一切都关乎于确认自己需要为朋友的自杀负多少责任。在所有角色于城市空间的游荡中,他们在质问自己,也在质问社会。他们最终选择了前往满洲里这样一种逃避的方式,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在长时间的内心独白后作出的选择。
《小丑》沉溺于描绘亚瑟的痛苦,并将其归咎于社会性的结果,但却不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哈姆雷特也同样痛苦,但让他伟大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质问。这使得《小丑》流于一种对社会的无因控诉,也让其展现出的同情失之廉价。
同情分为很多种。设身处地是其中最容易做到的一种。设想自己也被在肚子上捅了一刀,然后留下几滴生理性的眼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难。但这种同情,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对方吗?显然是不能的。与其说,这种同情帮助我们理解了对方的痛苦,但不如说是一种沉溺于自身的戚戚。更理想的同情,并不一定需要落下相同的眼泪,甚至都不一定需要为之而感到悲戚。若是我的痛苦中有着三分矫情和两分自艾,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你能比我更了解我,或许才是最好的共情状态。
若以此观之,我们对于亚瑟的理解或许只能停留于最肤浅的层面。将其视为一个悲剧,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始终站在所谓正常人的视角去看待它。而这种视角,未尝不是另一种排斥。在最极端的层面上,它最终会演变成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做到了一切能让你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还是不开心?”但为什么要开心?为什么要正常?
归根到底,人类在理解他人的苦难时总是失语的。将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只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在亚瑟每一个孤独的面对自己的夜晚,他会对自己说什么?他在对自己说什么?他应该对自己说什么?他一定思考过这些问题,但《小丑》中却依然选择用各种戏剧性的原因和结果去代替他本应存在的冗长的对白。
而我们听不到亚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