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何为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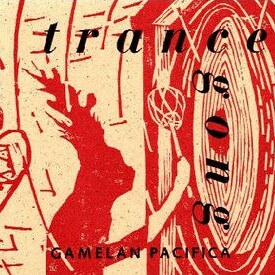
时间的永恒序列
不会是运动的机械延续
不会是生命的无谓耗燃
而是世代传承的朝向美善的远征
前方的跫音快将零落
但是,我认识自己的路。
—— 昌耀《山旅》
如果安妮·迪拉德读到昌耀这段诗,恐怕只会笑着摇摇头。 她应该会觉得这人很可爱,就像书中那位因宣讲进化论被流放中国的德日进。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们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总抱持着共同的执着,对他们而言,生命的出现不可能是一场巧合,生命的延续是为了让“神”的意志得到彰显,虽然对诗人而言,他的神是美与善。
一直记得昌耀这句诗,是因为我曾经也这么想。即使并无宗教信仰,传统教育还是灌输给我们一种世界观,让我们倾向于相信冥冥中自有“公道”在:“神爱世人”,或者“好人一生平安”,这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听上去很正确,但真的如此吗?我们这么想,是不是因为接受不了不符合人类道德观的世界?
迪拉德从开篇就把我镇住了:背脊只有一掌宽的鸟头侏儒、面容扭曲却智力正常的男孩女孩、安静可爱却注定早夭的婴儿…… 这些描述中有种猎奇的快感,既邪恶又悲悯。然而它是必要的,它强烈地暗示着这个世界的真相 ——
生命的诞生是一种偶然。生命本身盲目无序。我们必将死去,就仿佛我们未曾活过。
书中最让我困惑的是那些关于“云”的段落。她反复在提及那一代又一代人对云的记录,列举那些形状、日期、伴随而生的事件。那么多人热衷于对云的命名,可在无尽的变幻与不可复得中,命名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她在说的是徒劳之必要。
这是一本不太容易读的书。看上去二百多页的内容,不知道作者积累资料用了多久的时间,但对于一个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或许那些对比强烈的数字每次流经她的视线都会留下痕迹。而当它们被排列出来时,一种强大的震慑力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抬起头用彻底理性的目光审视熟悉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这是许多书中难得见到的。
比如第五章中“数”的一节——
数
N U M B E R S
地球上有1 / 10的陆地是冻原。任何时刻,地表上只有3%的面积在下雨。闪电大约每秒击中地面 100次。每个活人,包括此刻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大约每人可以分配1000磅的活白蚁。鸡的数量是人的数量的4倍。
我们中有1 /5是伊斯兰教徒。我们中有1 / 5住在中国。我们中近1 / 10的人住在活火山或休眠火山的范围内。我们中3%以上有心智障碍。我们每天要喝掉10亿杯以上的茶。我们有10000种语言。
我们中有1亿人是流落街头的儿童。有1亿2000万人住在非原出生地的国家。有2300万人是难民。有1600万人住在开罗。有1200万人驾小船捕鱼为生。有750万是维吾尔族人。有100万人在冷冻拖网渔船上。我们中每天有2000人自杀。
在这些庞大的分母之上,我们的存在是那个“1” 。
称迪拉德是梭罗的继承者,将她的作品视为另一本《瓦尔登湖》,是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作为读者,也很遗憾这本书的简介和书末的《跋》都在有意淡化她行文的冷峻,让人一开始误以为这是一碗温和的鸡汤。所以我能理解短评里有些人对这本书的不屑,因为如果你寻找的是优美的文辞和信誓旦旦的安慰,那么她近乎傲慢的诚实一定会刺痛你。
但《跋》中有一句提醒得很及时: “《现世》绝非一本神学之作,因作者本人恰是不信上帝的。” 在刚开始读时,迪拉德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史的叙述让我有一瞬陷入怀疑,对出生成长于无神论背景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种对神明存在和上帝意志的反复追问,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但如果将这里的神替换为我们熟悉的“天道”,就会发现这样的慨叹早已有过 ——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换回作者自己的话就是 —— 我们“承认我们只是区区雪花”。
那么,承认之后该怎么办。我们会因为道德的虚无陷入疯狂吗?毫无价值的生命也可能是神圣的吗?
书中有两段邂逅让我格外感动 ——
其一是作者在约旦河发源地的一条溪畔发现了一只青蟹。它意外的出现,让作者忍不住想找人分享,可她只等到了一位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于是在那空旷的荒漠之中,两个人对着同一只青蟹用自己的语言“交谈”。
其二,是她在海拔12929英尺的他泊山顶准备下山时,突然被一只温暖的手握住。那是一名患唐氏综合征的以色列女孩。女孩对她微笑着,在下山的途中一直牵着她的手,到了山脚下才回到自己的队伍中。
即使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个“1” ,但你永远无法找到两朵一模一样的云。存在本身并不神圣,但是对存在的命名,却让存在对人而言成为神圣。
非常喜欢这本书的结尾,探寻未知的冲动也许是人类最根本的神性。生命尽一切可能在这虚无的世界上铺展自己,生生死死,即使对宇宙而言它毫无意义,但它终归可以面对自己,去为自己赋予意义。
【曾于2017年2月15日发布于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