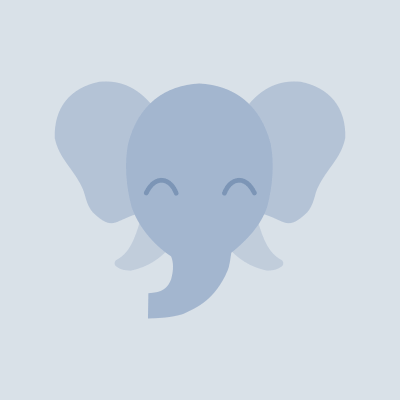#32 灯塔、黑暗之心、与恐怖谷
Day 32
湮灭Annihilation 2018亚历克斯·加兰

我太喜欢《湮灭》这部电影了,超越了我对最近几年所有科幻电影的喜爱。他太宏大,太复杂,诡异不安又细微致环环相扣。加兰从《月球》到《湮灭》简直就是为科幻片而生的啊。《湮灭》看完真是波谲云诡,暧昧的黄色云雾模糊了双眼久久不能平复,好似做了一个噩梦。
- 湮灭。湮灭这词不仅仅是五彩斑斓的“闪光”将会湮灭人类的栖息地,也是人类自身的自我毁灭。五人小队里的心理学家说“几乎没有人想要自杀,但几乎人人都想寻求自我毁灭。”好吧,还是老弗那一套死亡本能理论。片中的五个人几乎都是人类社会的边缘人,有些人反抗有些人随遇而安。最动人的画面莫过于物理学家扭头走向丛林深处,变为了“湮灭”本身Plant People的一部分。生命的终极形态:湮灭,即无形。但无形不等同于毁灭,而是亚瑟克拉克小说里的“超智”。
2. 克苏鲁与灯塔。克苏鲁神话中,那些巨大的,不安的触手系怪物往往来自深海,他代表着人类内心最深层次的恐惧。而灯塔总是作为“噩梦根源”的存在。在帕丁森的《灯塔》中,一种禁闭的幽暗也强调了权力与中心的地位会让人精神失常。灯塔是本该代表着希望,但是在深邃的海边,他也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这等于是灯塔在发出亮光的时候,他就能被看到,灯光熄灭的时候,他就是不安与噩梦的来源。

3. 无机与有机。豆瓣上有人说的很简洁明了“文科生看不懂《降临》就像理科生看不懂《湮灭》”其实两部电影我都很喜欢,但是更喜欢《湮灭》里关于生死,生命的有机循环。那些潮湿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形态,在片子是以生物基因学来讲述的。细胞的分裂,其实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万火归一。导演更为聪明的用生命伦理来解读这部电影,而不是站在一个神的视角。波特曼手臂上的那个衔尾蛇标志(衔尾蛇为一头处于自我吞食状态的宇宙始祖生物,它是不死之身,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总之人从肉体到液体再到气体,再化为世间万物的一部分,跟我们所熟知的生物降解一样,“无限大”,“循环”,我们都是“自我吞噬者”。当然也是”母体回归“,毕竟电影很多地方性暗示(灯塔-阳具、星团-子宫)很明显,不过我实在不想再提弗洛伊德了...


4. 《黑暗之心》。这应该是自《现代启示录》之后最接近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的剧本了吧。只不过《现代启示录》的背景是战争,《湮灭》是科幻,这种优势能让导演更天马行空的安排隐喻。《黑暗之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人类对自我的追求与探索是永无止境的,不管在哪个年代。而小说里的河流与丛林更像是血管与器官,叶的茎脉。
5. 恐怖谷。恐怖谷是用来形容人类对跟他们相似到特定程度之机器人的排斥反应。片中娜塔莉波特曼遇到的那个绿头苍蝇人就让人很不适,看的时候还把头稍稍扭开了。人类会不自觉排斥介于像与不像之间的生物体,就像整个“闪光”都人类认知里都存在于恐怖谷中。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乃至无法接受任何形态新物种的存在。影片最后莉娜差点被那个青铜色人体给杀死,而最终发现陷入恐怖谷理论的绿头人就是莉娜自己。那么“我杀我自己”后,她又提问“Were you me?"你是我那我是谁?

6. 虚无。最让我喜欢的就是电影从头弥漫到尾的虚无感了。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很多电影都把他做成一种制造悬念的方式,这很常见。可“闪光”是什么,从哪里来,导演提出了很多问题,却大部分都没有解答,甚至结尾也是开放式的。或许这时片子多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才是人类最诚恳,最卑微的答案了吧。导演用大量的废土和后现代美学充斥着整个银幕(有人说整部电影就是一个现代艺术展),完完全全一种沉浸式的观感,在这种视觉奇观下或许问题的答案并没那么重要了,只需感受那份绝望。也不知是导演故意安排还是演技不行,但演员的那份冰冷与麻木正在说明——我们不能理解,也不知道,我们毫无价值且脆弱。
7.原声。《湮灭》的原声实在太好听,不能说好听但是完美契合。Ben Salisbury 和 Geoff Barrow作为加兰的御用配乐师,《湮灭》对我来说超越了汉斯寂寞成为了近年来最棒的影视原声。轰隆隆的氛围浩室电子音乐震的我头皮发麻,不敢想象要是大银幕观影会是如何一番体验。

加兰的美学,哲学,心理学和艺术学储量之深和电影语言功力之厚让这部电影的所有缺陷在他的优点面前完全不足为道。对我来说这是超五星的沉浸式观感。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科幻片导演,完全期待加兰的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