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未必归一,而碎片已足够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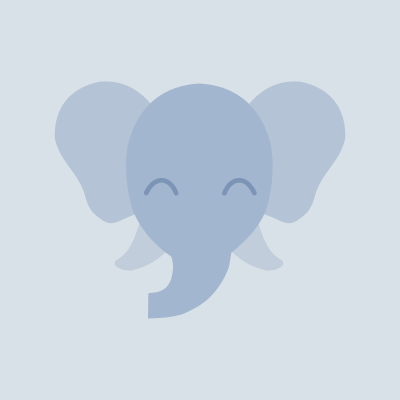
十年前购买的纸质版吧,不知道多少次翻到中途放弃了的一本书,今天终于从头到尾读完了。
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依然是讨论《浮士德》的第一章,大概因为在所有这些章节的详备、精彩的对文本、城市的细读并在此基础上串联的理论建构之上,伯曼对《浮士德》的细读最具向内掘进的“内面”/interority。他无比细腻地展示了,现代心灵和现代感性孜孜不倦的发展和扩张愿望,是如何与现代世界的扩张和翻新息息相关,甚至极大程度上就是后者的引擎。我想大概每一个在当代生活中受困于“自我成长”“终身学习”的欲望魔咒的人,无法不去察看自己灵魂深处的“浮士德人格”,无法不去共鸣知识和经验的攫取扩张也是一种发展逻辑向人心深处的延伸。
马克思章节中,伯曼似乎在有意识地调动文学批评的读法重读《共产党宣言》,深入理论文字展开的节奏,提炼意象并考察其历史流变——从成为本书题眼的“坚固”和“熔化”,到在莎士比亚《李尔王》、卢梭甚至波德莱尔处产生回响的“赤裸”、“面纱”和“光环”。到了波德莱尔章节,一方面伯曼延续节奏和意象阅读法,辨析“眼睛”和“光环”的复杂性,另一方面, 本书除了文学作品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文本——现代城市——开始进入视野。如本雅明一般,十九世纪的巴黎成为伯曼论述波德莱尔绕不开的参数。
如果说在波德莱尔章节,城市的林荫大道和碎石路上的车流提供了打开波德莱尔作品褶皱的必要语境性知识,那么到了彼得堡章节,城市就成了被考察的对象本身。从普希金、果戈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所有文学作品书写的都是彼得堡这座城市,它不仅作为舞台,更作为“欠发达的(自上而下的)现代主义”的自身,不断卷入希望在这座城市拥有属于自己定义的现代生活的男男女女的斗争。这一章对官僚/特权阶层与文职官员在大街上的冲突再现史,以及“水晶宫”意象所折射的城市现代主义和远郊现代主义的讨论都很有洞见。然而,也是从这一章开始,伯曼似乎开始大量依赖隐喻、象征和意象化的语言来连缀他的论述。文学不仅再只是讨论对象,也一跃成了他理论的展开方法。我隐隐约约觉得,这种论述方式在优美之余也难免闪烁其词,例如对“新人”和“地下人”的谱系学考察,伯曼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人”的更具现实感、内心冲突具足的版本,虽然别开生面,但也难免有削足适履,六经注我的嫌疑。对“水晶宫”的论述也有类似的问题:在波德莱尔章节平衡得更好的语境性知识和文本细读在这一小节似乎失衡了,大量的外延细节闯入并绑架了对文本自身的解读,使得最终的理论建构似乎也变成了空中楼阁。
不过,对远郊现代主义和城市现代主义的考察,也使得第五章对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的公路现代主义和大街现代主义的考察变得衔接顺当。这最后一章浸透了伯曼的私人记忆和情感,借流行语来说,我愿相信这是他这盘“饺子”的“醋”。其中最令我心折的收获是三个细节:
第一,伯曼对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女性主义解读,不期然间让我联想到,项飙曾经提出的火爆一时的概念“附近”、连接着上世纪20、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和60年代激进主义的“日常生活研究”,竟然有着鲜被提及(但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及缺乏思考!)的性别意涵!因为附近也罢,日常生活也罢,都是兢兢业业于俗世生活的女性们日复一日耕耘的领地!
第二,伯曼对雅各布斯这本书的批评,是它对大街现代主义过于田园诗的想象,其实忽略了种族和阶级的裂缝对于城市生活的冲击。这让我想到曾经看过的另一本引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著作,讨论纽约第六大道流浪汉的《人行道王国》。《人行道王国》引用雅各布斯,意在论证流浪汉对于现代城市生活有机性的贡献。但伯曼的种族批评提醒我思考,当《人行道王国》所描绘的第六大道流浪汉绝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的时候,作者对雅各布斯的白人田园诗的引用,是否缺乏了必要的批判性省思?或甚至,成了新的多种族版本的田园诗神话?这种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更新了对于之前读过的另一本书的思考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十分美妙的。
第三,伯曼在这一章追忆了童年记忆中温馨融融的布朗克斯街区,是如何被摩西的高速公路公共工程纵穿和摧毁。然而,他又提到,对布朗克斯的摧毁,本身即是遵守了布朗克斯内部的“基本道德律令”,即“出去,笨蛋,滚出去!”伯曼意在表达,内心深处对于更“现代”的“现代生活”的渴望,本身就会推动着包括他在内的万千年轻人离开这个街区,让它陷入空心化和溃败。所以,“我们大家”的灵魂深处都住着摩西。然而,他依然拒绝面对这一平行结构露出犬儒的、胜利的历史意志一般的微笑。在他心中,对更现代的现代生活的渴望,和由记忆深处的故乡被摧毁而生的心灵创伤,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这种“精神分裂”,正是现代人必然面对的暧昧、辩证、难以调和的矛盾处境。类似的结构,在当今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乡流动中,可以说也不罕见。
总而言之是万花筒一般的将诸种现代图景熔于一炉,并试图在其之上万法归一、炼就理论丹药的一本书。对伯曼理论建构的有效性和开拓性,甚至今天读伯曼的意义所在,我还暂时无法妄加评价,希望今明两天读读Perry Anderson和Peter Osborne的批评文章、延伸思考。但是万花筒的吉光片羽已经足够迷人。虽然伯曼诗一般的语言有时候让他的理论意图闪烁在神秘的暗示性中,但就其本身而言,语言结构之华美,论述气魄之开阔,已足以使阅读这本书成为收获满满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