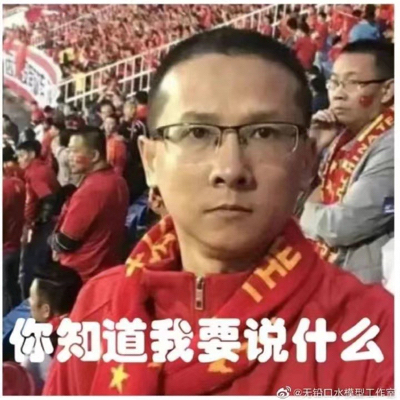女权即人权,人人皆“女人”
本书颇不易读,除了三度被书中言论击中而不由汗流浃背,更因为书本身的写法。”厌女“一词有着和”阶级“一般的鲜明性和共鸣感,是极好的社会学概念乃至社会活动术语,在一瞬间就将一些纷杂的现象提取出了本质共识。这种词甫一诞生就仿佛如常识一般,无需多言就能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论述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常识往往才更难解,其背后逻辑已经被完全内化,隐入心灵,所以作者借用了相当多其他学者和自创的概念体系,如弗洛伊德、塞吉维克、福柯等,后两者我无法多言,毕竟没怎么看懂福柯(权力的色情化一章实在读得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是很了解塞吉维克,并且”同性社会化欲望“是相当简洁有力的概念。但我对弗洛伊德的那套精神分析的话语却十分不以为然,在这套话语里,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仿佛不只是群体的代名词,而是有了自己的意志,像人一样有了渴望(与父亲同一化),有了行动(阉割),甚至有了情感(母亲对女儿的嫉妒)等,这种描述因为高度凝练的戏剧冲突感,而被文学家剧作家青睐(作者也非常多地引用了一些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情节,这自然又给阅读增加了一份困难),但对于学术而言,既缺乏实证的有力感,又缺乏理论的简洁通透感。
归根结底,还是弗洛伊德和福柯这两个老男人制造出来的概念并不本质。在我看来,要描述社会现象,使用权力、资源等政治经济学概念,采用博弈、演化的思路,辅以个体意识的自我维护、认知协调等心理需求,用这些更本质的概念,即可解释全部的行为。换言之,无需特别引入”男“”女“这样的对立概念,完全通过数学结构,父权制社会、厌女也必然会出现,也必须要反对,也必然无法彻底消灭。
在读这本书时我一直在试图琢磨一件事:到底怎样才算作”不厌女“,作者一开始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一直描绘不同群体和场域中的厌女现象。直到读到最后一章时,作者才试图给出答案,但却很客气地告诉我们这些男性读者,男人如何不厌女,如何与自我和解(因为男性厌女也会导致与自我的不和解,这是另一个我既颇为震惊又不以为然的论述,震惊之处在于男性对身体这个第一个他者是如此地无情,以至于无论是五毒俱全的损害,还是自虐般的训练,都代表了一种强烈自我厌恶,这对曾经熬夜和暴食双杀,曾经和正在自虐般训练的我而言,无异于指着鼻子在嘲讽了;不以为然之处与上相同,这种思维方式也太特么弯弯绕了,”他者“这个概念就是又一个无聊而又流行的创造,无非是想说明一种工具性的存在,然而谁能完全逃离工具性的存在呢?当自我意识是这么一团”目的达成机“的时候,什么不是它的工具呢?)是男性自己应该寻找的答案(尽管我认为她给女性的答案也并不清晰,竟然只是简单的自我和解??)。好吧,也确实如此,但这个答案颇不容易寻找,甚至我寻找的过程中似乎在进行另一种”厌女“行为:在弱化”女性“这个标签,看起来像是给男性脱罪一般,但这当然不是我的目的,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先抽象再还原的做法。
探讨如何算作不厌女,我想从起点出发,在一个假想的最初的最初,”男人“和”女人“最初的分化是什么?我认为只有一点:直接的身体暴力(男)vs生育能力(女),如此而已,其他再无区别,其他所有生存能力/需求、艺术与感受的能力/需求以及因此衍生出的抱团/竞争等社会需求,甚至提起火箭筒轰杀对方的能力(非身体暴力),都没有差别。换句话说,除了身体暴力和生育外,其余都属于”人“的领域,包括纯粹为快乐而开展的性,也属于”人“的范畴,是无性别的,唯独暴力和生育是属于”性别“的范畴,是双方所独有的。近代女性能够在政治经济地位仍与男性有较大落差的情况下逐渐开始觉醒,无非是因为直接身体暴力的效用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极大抑制和削弱,而少子化等现象让社群对女性生育能力的依赖更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形势有了颠倒。而男性如今还能够实施剥削和掠夺,依赖的无非是几千年身体暴力史积累下来的优势,是在吃老本。
从这个角度讲,男人的”男“的那部分,天然就是罪恶的源泉;从这个角度讲,女性应该对所有男性保持警惕,无论他表现得如何热爱女性、热爱平等,像个女权主义者那样,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人“的那部分被”男“的那部分压过。
扯远了,但这些已经接近足够解释很多东西,比如男性社会化认同,上野认为男性必须拥有一名女性才能进入男性共同体,按我的说法,上野的认识还不够彻底,这种传统的雄性间的认同更基于暴力语言,别说没有女人,就算是温柔地对待一个女人,都会被视为不够爷们,不够男人(耙耳朵、妻管严)。比如“男人更在意别的男人,而将女人符号化”,因为暴力与生育不同,暴力有高低之分而生育没有,没几个人会和人比较谁生得多生得快,然后觉得自己很牛逼(生得好不好属于被男权扭曲后的比较方式),但暴力之间是存在鲜明直接的对比的。暴力后来演化成了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机构,而生育则连带着与之紧密相连的性的快乐,一同成为男权社会的资源被暴力攫取。
书中许多描述其实并非男女之间的特例,而是强弱之间的典型,比如某章说失足女通过给嫖客定价来达到羞辱男性的目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弱者绝望的复仇形式,实际上只有很坚韧但又很无奈的自我解脱的味道,对加害者没有分毫的实质伤害。刚刚在豆瓣还看到个早年被霸凌的女生长大后找当年的霸凌女生讨公道,反而再遭羞辱的案例。其余相似之处不必多言,厌女是种种厌弱现象中最鲜明和最普遍的一种,也正因为如此,女权即人权,人人都可能成为“女性”。(这部分也就是我说的弱化了男女标签的地方,但强化之处已经如上段所述)。
最后,除了“男性自我厌恶“那段,另两处让我汗流浃背的描述,一处是”男人更在意男人,而将女性符号化“这一点,惊讶之处在于,曾有段时间我惊奇地发现,在遭遇竞争时,我根本不在意我自以为喜欢的那个异性的感受和选择,而是在意她与谁出去,”那个男人“如何如何之类的东西。如果看到那个人优秀无比,那就黯然神伤;而如果发现那人看起来不值一提,就会相当程度地释然,觉得女生眼光不过如此;另一处是春宫画那章,所谓”男根中心主义“的念头,我似乎也不自觉得有过一些。所以在读到此二处时,我有种被说中了感觉。
所以我才要说,对女人来说,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警惕;而对所有的男”人“来说,也需要不断警惕自身”男“的那部分,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从”人“,变成”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