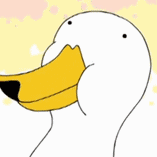对海德格尔的反叛
在海德格尔那里,没有真正的过去或将来,只有共同构成当下的作为整体的时间性。“向死而生”,是此在的职责,是直面死亡承当起本真存在的英雄的任务。而在列维纳斯这里,死亡永远迫近却绝无可能被“我”所掌握,“克服死亡”不过是主体的幻梦,当死亡来临,“我”已不在。“死亡就是筹划的不可能性”。但同时,死亡的绝对不可把握也展现出一个真正的将来,在死亡中,“光”的经验被打断,客体停止朝向主体回归,“我”的绝对在先被废除,绝对异质的实存、匿名的 il y a在此显现。“死亡不再是肯定而是打破了我的独在”(p62)。这就意味着实存是多元的,而非只是不可逃脱的、统摄一切的实存。他者在此与我一同分担一种共同的实存。他者不是“向我显现”的,但也不是马丁·布伯所说的,“他者在先”,他者只是如死亡一般绝对的不可知,不可通过光而复归主体自身的存在,是使主体不再是主体的事件,在此,黑格尔的主奴之争从未开始,遑论把捉、认识、掌握这类彰显着主体之权能的词汇:“我”已不再能有所能,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回到无能呜咽的幼年。经验在此遭到毁灭,因为经验已预示着“我在”。只有接受死亡/将来的异质性,容许死亡被迎接,战胜死亡的企图才有可能在失去“光”的巨大恐惧中得以实现。与他人面对面的相遇也是同样。“在其中事件朝向一个不承担它的主体发生了,这一主体决不能与其相关,但是它却以某种方式位于主体面前。‘被承担’的他者就是他人”(p67)。在现在与死亡的深渊之间,在与他人的遭遇中,时间出现了,。“时间的条件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或位于历史之中”(p70)。“他人恰是我所不是者”(p77),他人不是我的ego 的投射,爱、同情与理解,并不因他人是另一个自我而发生。“情欲之乐的哀婉在于存在着二”(p80),柏拉图合而为一的爱欲永不可能实现,与爱人之间永不可能跨越的深渊也意味着,主体永远面对着他人,也永远欲求他人。爱欲意味着一种失败,意味着那种为自由的胜利而起的斗争从未开始。“爱不是一种可能性,它不源于我们的主动性,它也没有理由,它侵入我们并刺伤我们,但是我却在其中存活”(p84)。爱是完全的神秘。列维纳斯就此,将海德格尔的永不出场的sein、统摄一切的死亡转变成爱欲。
正因彻底的不可知、正因不可理解(前面已经说过了:认知和理解这类带有黑格尔的斗争意味的词汇无法用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拥有、知道和把捉是权能的同义词”(p85)),正因我只能“在期待之中”,爱才显得弥足珍贵,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