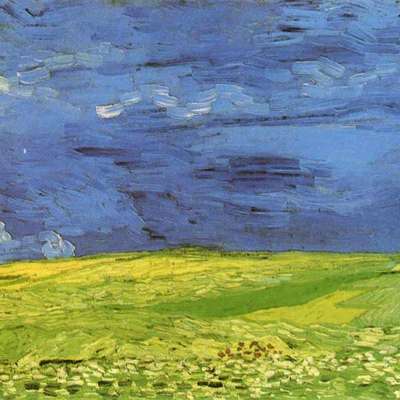审判的历史维度与展开
一、概述
审判,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既具有十足仪式感,又有其深层的,从属于法的终极价值的意义在,即实现公平正义。从这一角度看去,现实中许多审判脱离了它的最终目的。故可以说,探寻“审判为什么不公正“的价值巨大。但同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本书从“历史的“这一角度切入,避开深奥的理论阐述,向读者展现西方,也仅仅是西方的审判史。此为第一层展开——历史维度的展开。全书共分八章,大致涵盖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从两河流域到爱琴海,从地中海到西欧,从不列颠群岛到北美洲等等。
第一个阶段始于古巴比伦,终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其中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们是彼时西方历史的重心所在。
第二阶段始于中世纪,终于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此时作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教权和王权主导下西欧的司法情况:除了教庭对巫术、动物、尸体和物品的审判外,还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系——纠问主义代表的大陆法系和陪审团制度代表的海洋法系。
第三阶段就是从现代社会诞生到目前的时代。苏联的肃反运动、对战争罪的审判以及陪审团制度的变化成为主题。
二、审判史
从历史维度衍生开去,审判的内在被展开,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具体地把握它和历史的关系。
(一)起源
审判的缘起在于神意,因而它可谓十分牢固。可卡夫卡之言“仅仅是时间概念让我们称其为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道明了其根基并不牢固,它总是在变化。这句箴言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或许世上并无神的存在,或许没有谁能够真正审判谁。
审判的最初把持者多为权贵阶级,古希腊人则展示了它的民主一面。书中所举之例乃是戏剧《俄瑞斯忒亚》。面对着永恒存在且永恒刁难人类的道德困境,古希腊人用民主制度和公权约束着残暴的复仇欲望,彰显自己对于民主和人类正义感的自信。我感叹于西方文明的公民化开始之早,我国相比之下一直处在家天下的世界观中。
从古希腊的司法实践中就可以看出正义这一概念的复杂性。譬如作恶者是否无论其意识理智与否都要担责?在后续的一些章节中,如审判动物、尸体和物品这个争议也有出现,且时人对此的解答已与古希腊不同;罪责的承担者应是什么?(古希腊有许许多多的荒唐仪式,企图摆脱或者转移罪责);对于作恶者的感性上的嫌恶是否需要进入制度考虑范围?(古希腊人相信杀人者会散发臭气,而有罪者肉体不洁,故他们在审判中设计了一些仪式来封闭被告人)等等诸如此类。这些争议贯穿了人类的审判历史。但此处历史的吊诡显现。非理性的精神,与理性一样,同样拥有滋生法治观念的能力。
(二)中世纪与近代
中世纪的宗教猛烈影响着欧洲的法律。诉诸于不可为我们理解知晓的命运之神,神明审判相信造物主的全知全能。主要有两个例子。一为共誓涤罪,一为神明裁决。材料表明,当时许多人相信如此做的正当性。启蒙运动的意义可知矣!这种仪式仅有恐吓作用而已。
巫术审判,动物审判,尸体审判和物品审判出现在中世纪。
在巫术审判章节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580年让·博丹出版的著作《巫师的魔凭狂》中提出的观点:处理巫术这类严重威胁道德秩序的犯罪时,无需保护被告人,而是应不择手段地实现审判。恐怕巫术也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一种迎合权力的手段。因而我们必须认清那个时代。究竟是狂热的信仰作祟,还是阴暗的欲望的隐发,亦或两者皆有之,甚至于更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7世纪末的塞勒姆小镇可以寻得。有证据显示,塞勒姆处死的人数,可能多于之前美国殖民地处死的巫师的数量总和。隐藏在表演背后的原因则是土地纠纷下各阶层利益冲突严重而无法正当调节。丑恶的时代,让人想起文革。在这种审判面前,我们再度面对正义和惩罚。惩罚他人的欲望伴随着对自己理念正当性的无比坚定,造成了许许多多悲剧。
在动物、尸体以及物品的审判中,活在混乱世界中的人们渴望寻找到一种秩序感。或许是世界太过复杂,犹如被狂风掀起巨浪的海洋,而人类的意识,仅仅是其中的一叶扁舟。(进入现代社会,科学代表的理性虽然给予我们智识上的清明,却无法捕捉生活惊涛骇浪般的鲜实血气。终极价值从我们的生活中脱离。一切虽被怀疑重置,但一切的重担压在了一个个无助的心灵之上。我们的时代命运便是诸神之争。)
随着神明审判的解体,欧陆兴起供认之风,并持续数个世纪当时权力背景大致是教权与王权的结合。教会法的纠问主义深刻影响了欧洲的世俗法律。它成为大陆法系纠问主义的渊源。欧陆王权也受着这一有利因素击败了教权,完成自己对于国家的完全掌控。趋极的君权带动了隶属君主的官僚的权力的膨胀。司法权力亦然。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终结了纠问式审判。而英格兰因其较为独特的传统而走上了陪审团之路。陪审团制本身包含几乎可以忽略的刑讯使用以及公开化的法庭。相比欧洲大陆的纠问主义,它迈入的是正轨。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力来自大宪章精神以及光荣革命对封建王权的约束。
(三)现代
不得不说,法律是迎合所谓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法律具有阶级性,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无论现代或以后的法律怎样更加文明,它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想,没有人们对于不公和奴役的憎恨和奋起反抗,法律也不可能改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培养起这种精神,同时也受她反哺。从这个角度看,审判的历史其实就是整个历史的缩影。
莫斯科审判秀处于苏联大肃反的历史宏观背景之下,极权国家机器的车轮碾过许多个体。在这里,我们看见历史惊人地重复。权力的游戏再次上演,一如巫术审判一般。归罪,自我归罪,只有红心是我最爱。布哈林的陈词如下。
三个月来,我一直拒绝发言。然后我开始作证。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做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如果你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个绝对黑暗的空虚突然在你的眼前升起,逼真得令人惊骇。如果一个人想在死去的时候毫不后悔,那么没有什么是值得你为之献身的。相反,一切在苏联闪耀的美好事物,让人的心灵展开了崭新的向度。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点是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他的挣扎,便是那时所有人的挣扎。斯大林严酷处理国内,却要求公正处理纳粹战犯。美军在越南犯下滔天罪行,回国后却免受法律惩处。发动南斯拉夫内战的领导人在公开法庭上却成为了本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战争审判的戏剧化贯穿其过程和结果。审判背后的政治宣告一直存在。以上章节都在诉说一个道理:各因素的角力、冲突、妥协和再平衡才是现实的处境。
同样提醒我们不要把法律的实行情况理想化的还有陪审团制度。《十二怒汉》讴歌了它。可现实情况远比电影更具戏剧性:在各类精彩的人物面前,嫌疑犯成为了最无足轻重的角色。法官们在审判戏剧中扮演法的看门人一角,他可以让门外人轻易进入法,也能让门外人终生游离于法的大门之外。陪审团做出决断,基本上不是基于其智慧。极端情况下一些陪审团会求助于骰子或者祈灵的巫术。更加令人绝望的是,越是想要尽自己职责,从而十分关注法庭上呈现的证据陪审团,越发容易犯错。面对案件,无论陪审团还是更专业的法官,都在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非辨认对错。真正重要的是,正义必须根植于信赖。如何做出赢得众人尊敬和信任的裁决才是审判的核心难题。另一方面,法官相比陪审团而言,更容易做出有罪判决。这并非是因陪审团更富同情心,而是他们的十二人的多样性(密尔的观点)能够抵消许多不足。因而作者相信,如果改善陪审员的选拔制度,使得他们真正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那么陪审团制度将比一人独裁的法官制更优越。
三. 总结
刑事审判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供奉着一个信念:面对惩罚时,首先深思熟虑,再作判断。然而保护无辜者的理想总和人惩罚有罪者的原始冲动相冲突。近些年来,后一种欲望衍生的观念,即犯罪必须被惩罚,得到了发展。司法一方的权力被扩大,被告一方的权力被限制。同时,惩罚的意义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重新发掘,并且以媒体可以不受限的报道任何刑事诉讼的方式得到法律人士的认可。他们一同认为公开审判对社会有着重要的疗效作用。然而,庭审直播滋生了公众对正义实现的期待,或者可以说是看客心理,无罪推定原则失效,法律的执行变得严苛。
刑事审判展现了人类的尊严——人类必须文明地活着。但对于正义的过分追求又往往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