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的某份期待是如何被杀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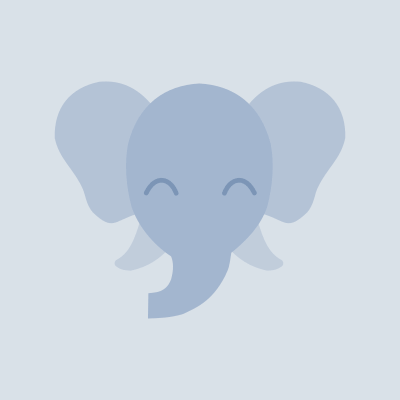
浪姐能成为大爆节目,不仅仅是因为30位30+女性聚在一起的结果,更是刚开始成功切入职业女性的视角,才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讨论度。尤其是刚开始两期,对于这些女性的群像展示更加勾起观众尤其是女性的感同身受。 其实大家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其中大部分的明星都不需要真的成团,她们缺的并不是这个出道名额,而是接了一份工作能够增加自己的曝光量,顺便可以展示自己一些以前尝试过/未尝试过的职业技能。这一点从第一次舞台SOLO和公演都能看出来,大家选歌和练习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职业技能/舞台预期去选择,所以大家对于这两场的评价也会特别高。 然而,一切都从第一次公演淘汰后,这套系统就开始崩坏。其实这里的问题并不出在“淘汰制”上,反而这是节目组很精心选择的一个方式。对于这群职业女性来说,要她们能够乖乖接受这么大的工作负荷量以及与其他竞争对手合作的任务,就是靠“组团”这个噱头在困住她们。大家都意识到,“自己好”不仅仅是不够的,更是不对的。而且团员的淘汰也意味着自己同样需要分担这份责任,所以她们必须要在保证完成自己的任务同时,去带领自己的团员。 这其实本身是一件好事,然而一公赛制设置的不合理以及观众的音乐水平有限,导致了“单纯展示唱功”这件事变成了“危险”的事情:如果想要继续靠展示演唱去比赛,很有可能会获得低分,就意味着自己这团的失败,而比起自己被淘汰更危险的事是队友被淘汰。 原本如果只是“自己有可能被淘汰”,很多姐姐很可能会为了留下好作品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可是就像前面说的,这一选择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队员被淘汰,这就使得许多姐姐在选择上必须屈服于所谓的“事实”。 这一点其实很可悲地反映在许多地方,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职业生涯。 这一切在二公里被极大地放大了,节目组对应的“资本”以及音乐素养有限的“观众”在有意无意中联手成为了绞杀这30位姐姐职业表现的凶手。 节目组要的始终是流量与资本,它们要头疼的是如何将所谓的“皇族”在合理的剪辑下面让她们顺利出道,这才能够使得节目组获得应有的资本。许多观众其实没意识到,节目组要流量是为了更大的资本,所以很多人真情实感地问为什么不捧谁谁谁难道不是更吸引观众吗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节目组“为什么需要流量”的真正原因。事到如今皇族究竟是谁已经非常明显,很可惜的是节目组并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剪辑能力将这些皇族的镜头剪得让她们的“努力”配得上相应的“镜头”,导致了观众对其的叛逆。 然而,事实并不是“资本想喂什么观众就愿意吃什么”。消费者始终不是单一的被输入方,如果仅仅是节目组在一味输出自己的观点,倒也不至于翻车成现在这样,毕竟熟悉演艺圈的我们都知道,有皇族才是正常的,只要能够保证其他人还能够有一定的镜头与剪辑,观众骂归骂,始终不至于到厌倦。 问题出在,从现场观众的投票来看,市场就是喜欢这一套。 虽然很多现场观众都辩解是节目组的赛场设置问题,对观众的不合理要求,以及比赛赛制的失策,然而不仅是从具体票数以及网上的讨论度来看,观众就是会倾向于选择“燃”“炸”的舞台。就算像《仰世而来》播出后能在网上引起讨论,但像《相爱后动物感伤》这样的作品就明显低了好几个讨论度。然而《动物》的完成度可以说是整个二公数一数二的,不仅仅是加入vogue元素的改编,还是在舞台的呈现方面,尽管后半段节目组的打光与拍摄上拖了后腿,但依然非常亮眼。可是这样的作品始终属于小众,它并不是“作品不好”,但是却因为理解的人少则连播出后的讨论度都难以跟上。这就很难单纯地指责节目组。 观众的选择有心无心地成为了帮凶,导致了这群姐姐们必须有所舍弃地一味选择能够引起观众喜欢的作品。观众一边感慨节目的单一化,一边又忍不住为更燃更炸的舞台投票,结果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赵兆说的“音乐没有高低之分”其实是并不是真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一个评分体系下,就是有高低之分的,而这一套高低之分又和所谓的音乐专业标准并不相对应。观众的“听不懂”成为了节目组与资本手里的一把刀。 于是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浪姐彻底没了刚开始想要改变30+演艺圈女性甚至职业女性现状的可能。 那有错的只是节目组和观众吗?当然不是。某些媒体批评浪姐的娱乐性,对女性议题的忽略其实是可笑的。骂观众鉴赏力不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故超越自身的阶级,骂节目组骂资本表面上有意义,但它们最多忌惮一时片刻,当它们发现观众喜欢的还是这套时依然会卷土重来。 正如我们对许多“烂片”“神曲”的爆红难以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阶级也是处于被无限撕扯拉大。所谓的“品味”本身就是阶级化的,对于“什么是好的作品”这一回答本身就会牵扯到你对于自身文化资本以至于你所处阶级的理解。可是在当下连“阶级”二字都成为敏感,不去直视病灶却寄希望于一个节目去承担这个社会议题,真的很不应该。 可惜的只是刚开始大家好像看到了什么可能性,结果现在又黯淡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