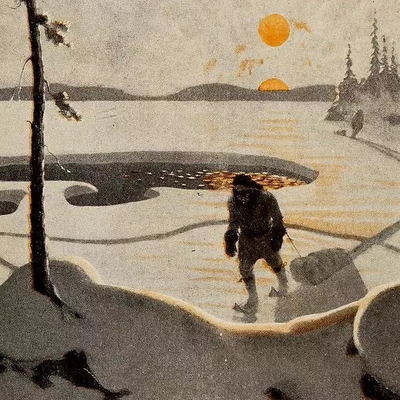天真而神化的信仰
「这世界真说不上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反正它是越变越快了。」
——顾城
我先总结一下全书结构:
在第1章里波兹曼阐述了媒介的力量,先强调“媒介会对我们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然后在第2章里详细地定义了“媒介”;第3章阐述了从美国的建立到19世纪初,铅字文化是如何蓬勃发展、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在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中的;第4章描绘了在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影响下的美国的文化是怎样一幅盛况;第5章阐述了19世纪中叶开始,以电视为基础的认识论如何开始取缔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第6章阐述了以电视为基础的认识论存在怎样的问题;第7章至第10章分别从传媒、宗教、政治、教育这几个角度对那些问题进行了具体刻画;第11章做了最后的总结,回归到波兹曼的初衷,即他并不是在抱怨电视的存在是错误的,而是希望人们认识到,电视作为一个媒介让人们形成了新的认识论,而这样的认识论存在许多负面影响,人们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思考方式。
值得强调的是,波兹曼希望我们注意的是“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并不是“电视”这个工具本身。是“以电视为基础的认识论”导致一切产业都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导致人们不再崇尚真实,导致人们欣然接受所有过量、零散、无用的信息,并始终沉溺其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论述文集,看完这本书后我终于发现了为什么自己做毕设时看的大量那些同样是论述文的文章、书籍会让我浑身难受——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啊。
分段记录一下自己读这本书时产生的思绪,段落之间有先后顺序,但没有承接关系。
[一]
「人绝对是无可度量的,人处于不可度量的位置,他用可度量的事物让自己可以表达。」
——路易·康
我看到波兹曼对钟表的说法后想起了康的这句话。波兹曼受芒福德的启发,写下“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单独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这时候再想起康对于Unmeasurable和Measurable的叙述,对“发明”、“创造”、“表达”、“传递”、“记录”这类行为就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理论(?)的衍生之一便是《你一生的故事》(电影《降临》的原著小说),这个故事就是围绕表达方式对认知方式的影响而写的。小说里着重刻画了语言对高等生物思维的影响,在这个例子里,“语言”是塑造高等生物、区别人类与七肢桶(外星人)的主要媒介。人类通过研究发现,地球与七肢桶生存星球的物理原则一模一样,但双方用来表达相同规律的公式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的语言导致了我们对同一个物理环境的理解不同。波兹曼在第2章里写,“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二]
第4章特别好看,它描绘了林肯与道格拉斯在集市上激烈地进行政治辩论的场景,看得我有点热血沸腾。其中对环境的描写让我着实意外,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
这段环境描写让我想起了《奇葩说》——以辩论赛为内容主打的网络综艺节目。
《奇葩说》是一个典型的“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影响下的优秀的网络综艺节目。19世纪中叶,林肯和道格拉斯的严肃的政治辩论,其环境也不过是普通集市,人们虽然对其辩论内容抱有高度热烈的关注,但也有人在一旁交易买卖、娱乐嬉戏。而与《奇葩说》不同的是,他们二位演讲者所用的复杂语言是当今电视节目嘉宾们完全不能想象的。我当然不是说嘉宾们没有能力说出复杂微妙而严谨的句子,而是观众们不会希望听到那样的句子,所以嘉宾们也并不会做出那样的努力。在电视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娱乐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演讲者只需要让自己听起来好有道理、吸引眼球并赢取感情就可以了。
「很难想象,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要不是因为关注李诞,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网络综艺节目,每次他上一个节目、发一条微博,我都会点进去看看(论真爱粉的自我修养),结果是每次都会看到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的后期特效,给我的感觉是有很多垃圾在从屏幕里向我砸来。这是一种刻意分散观众注意力、希望通过视觉效果来填补空白内容的方法,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与之相比,李诞他们策划的《吐槽大会》可以算是一个很严肃的网络综艺节目了,它将每一分力气都用在了演讲者的话语里,希望直接通过他们的讲话内容与表演技巧(包括话语节奏与肢体语言等)来展现幽默。
[三]
第5章里,我无法完全赞同波兹曼对于照片的阐述。
「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波兹曼所陈述的事实在他的语境下都是对的,可是这一语境放在更大的环境里就有了不适用性。他说报纸新闻上的那些照片,对,他说的没错,但照片只是报纸新闻上的那些照片吗?
优秀的摄影集,摄影师们是严格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编纂的,编纂思路体现了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可以被阅览者感知,并且被感知(哪怕被误读)才体现它的意义。
我并不认为不严肃的形式一定无法表达严肃的内容,也认为哪怕波兹曼已经很好地做到了客观严谨,但还是过少地描写了电视文化的正面信息。他明显地主观上反抗着电视文化带来的大部分结果,其实我也倾向于此,只是认为他可以论述得更加充分。当然,我不应当对他有此苛责,毕竟我们所处的年代不同,现今电视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任何影响、无论优劣,应当都已经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了。
波兹曼低估了摄影的力量、电视的力量,我说的是哪怕在他的语境下也可以作为正面存在的那种力量。他没有刻画那些(可能是他不知道或者他那个年代还没有吧),我想这是他的局限所在。我不认同他对照片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不认同,只是可以提出反对观点),不认同他将主要问题归咎于媒介的导向。他说“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可是是这样吗?本质上来说,是利益在引诱人们这样做啊,所有媒介的推广都不过是受着利益的牵引。
[四]
当一件事情“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时,我们究竟要如何评价它呢?
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可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啊,从何感到痛苦呢?这结语简直是太过居高临下了。
[五]
早年的知乎真是铅字文化的典范产品,为什么现在会充斥着大量不明所以的故事和滥竽充数的机灵?因为在当今这个年代里,事情本来就会如此发展,这是利益所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好这一工具,不,障碍并不体现在工具的使用上,障碍体现在生活的其它细节里。
社会里的一切事情都是以利益为前提而发展的,这本身是没有好坏性质的,对利益的追逐要求人们提高效率,而为了“提高效率”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了新的问题,尤其是现今的中国。我只是在陈述这个现状带给我的困境,以及思考自己要如何应对,并非抨击它的不是。这个时代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它就这样。说到底,促进社会变化的终归是利益,以前如此,以后也是,有什么好坏之分呢?
[六]
我终究还是非常喜欢这本书,也非常认可波兹曼的态度与付出的努力。波兹曼说,针对这一危险状况的希望渺茫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学校”。
「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
“天真而神化的信仰”,我十分喜爱这个短语。
或许我比波兹曼更加悲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更加乐观。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不可能、但也根本没有必要得到解决。这一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悲伤,但它本身并不悲哀,也不需要得到改变。我们做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只是因为我们必须为了自己去做。所以重点从来不是“人们是否保持着这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而是“我是否保持着这一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是我以及其他一些喜爱这本书的人们获取力量的方式、生存的方式,并非这个社会需要聆听的苛责。
[七]
这书真的太好看了,令我感到畅快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