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学——对人类个体的终极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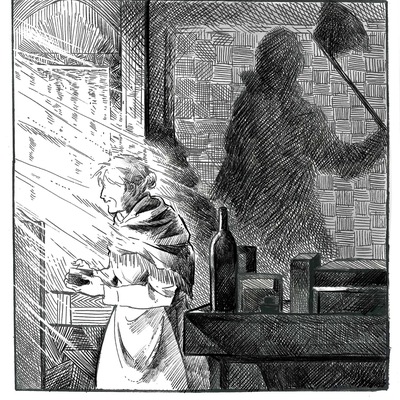
宇宙学有什么用?
对于普通人如我,看看宇宙学的科普大概类似一种心理按摩吧。
人类太喜欢自己,习惯于把自己当成中心。当随着本书开始那一系列天体大小的类比一起追溯时,人类已经没有了位置:这个类比的起点始于地球,途径银河系、仙女星系、室女座超星系团、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斯隆星系长城,终于可观测宇宙。在这个比喻链条里,距离以光年为单位指数级增长,平均身高170cm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引以为傲的事,也不过就是观测。
人类的无知构成了人类的认知。我们假想宇宙静谧,行星和恒星默默地、缓缓地运动,因为真空阻断了声波,而我们无法将电磁波用感官捕获。我们想象遥远天边的星系发着暗淡、柔和的光线,因为我们还无法很好地理解超越几十亿光年的、来自过去的星际图景。城市的灯光从未停息,我们迟钝的肉眼看不到直径几万光年的庞大星系,而它正以我们认知到的静谧的、缓慢的方式,将我们——整个银河系——吞入腹中。
多么美妙啊。人类整体的定位的失重感让人类个体得以迅速地从人类整体中间抽离——从而奔赴更大的整体。不会再有任何其他更好的方式让人类个体认识到存在的实在性——更加巨大的实在性,不可辩驳地存在着。人类个体除了存在别无意义,情感、关系被迅速化约,个体被迅速合并同类项。人类个体以人类整体这一最小实在单位而被整个宇宙实在的存在肯定着。
多么美妙啊。没有任何一种集体主义可以给予个体这样的肯定。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我能从宇宙学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吧。
回归到书本身,在看开篇的天体和城市-国家-大洲比喻的时候,我尝试在白纸上开始画图,结果在画到室女座超星系团之后A4纸就画不下了,只好另外用了一张纸。

画了一半就画不下的室女座超星系团

草草画的可观测宇宙
我们熟悉的地球被比喻成一颗玻璃珠,太阳系是一栋别墅,坐落在银河系这个城区的荒凉地段里。而银河系城区也不是中心城区,只是在本星系群这个城市的普通城区。甚至本星系群也不是省会城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城市。
但即使是这个普通的小城市也发生着摧枯拉朽的剧变。作为本星系群中心城区的仙女星系是人类肉眼可见的最远天体。这个质量是银河系2倍的星系的中心黑洞质量达到了银河系的30+亿倍,正因为仙女星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断吞并星系的“侵略者”。在潮汐力的作用下,与仙女星系遭遇的矮星系的外围物质被剥离到只剩核心,而银河系也将在50~70亿年后与之狭路相逢,只有被动接受吞噬或被抛弃的命运。
如果几十亿年还有人类,他们记录下来的天空的图景将会大大不同。我们现在观测到的银河系长长的银练旁将出现螺旋状的仙女星系的全貌,两者跨越几十亿年的撞击过程中,迷幻的散落的漫天亮斑次第出现和湮没,从此天空的景象将被改写。

模拟的仙女星系碰撞银河系的过程
想到任何人类个体,甚至人类整体都不一定可以亲眼见证这个过程,就真切地感同身受了“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些鼓舞人心的理论,比如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但不管怎么说,认识无知与有限远比重拾信心更重要。
最后是一张通过对大、小麦哲伦云的观测证明了造父变星是一种可以用来测量遥远宇宙学距离的标准烛光,从而开创了现代宇宙学的Henrietta Leavitt女士的图!因为书里没有她的画像,所以特地来贴一下这位伟大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