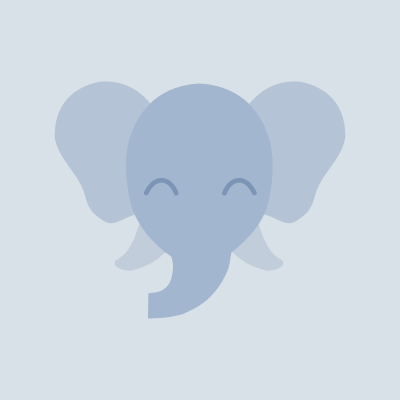叶荻,你一定不懂吧。
写类似题材的作品不少,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作,还有《所罗门的伪证》《时间停止的校园》这两部。
不过,《樱草忌》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某几个情节上产生了既视感,这还是一本完完全全的“新小说”。当然,这个“新”有好有坏,同样,这个“新”其实藏了很多的“旧”。
先谈谈故事吧——
故事发生在2016-2017年,讲述了一位“文学少女”林远江用死亡向整个社会复仇的故事。腰封上的“反本格宣言,反青春小说”是完美的概述。关于“反本格”,最明显的就是主角之一的林远江对于本格的嗤之以鼻。此外,在整篇故事里用到的唯一手法是叙述性诡计,还是“即使是推理小说入门者也能够一眼看破”的简易诡计。而姚老师,这位在前作中大放异彩的“侦探”,提出的伪解——林远江的母亲为了洗白自己是杀人凶手而伪造日记,似乎也完全站不住脚。她在煤气杀人未遂之后的公开日记和“伪造日记”与伪解还算靠边,之后的举动却显得完全与伪解不合。如果她为了洗白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大批网友的暴民性和猎奇性,用有限的公开林远江的日记和记录自己在女儿死后的悔过自述洗白自己,同时给叶荻扣上一个不知悔改的帽子,然后安然自得的过起新生活,有时间再发几张律师函起诉叶荻一家。结果可能会是败诉,但她通过事件累积的名声足以让曾经也是个“文学少女”的她成为一名女性写手。我认为一名懂得诱骗还算聪明的女高中生进入自己的死亡陷阱的曾经有些许才华的女人,绝对有这样的本领。退一万步说,就算最后一事无成,她回到曾经工作的地方,少了一个女儿的她在之后也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甚至于能够买下那套精装的一居室。姚老师这个无法和“舆论控制”这种本文核心观点自洽的伪解,再加上“作案”手法的匮乏,“反本格”也就在意料之中。
那么“反青春”呢?腰封上林千早老师将它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了归纳,在后记中她指出这是“文学少女”被戕害和被迫反抗的两条路。在我看来,这两本书中的少女形象是大有不同的,房思琪比之林远江,一个早慧,一个偏执。尽管两人最终都走向了毁灭,可是一个是将浮华的外物撕裂,把一直想要保护的美好内在也毁灭的故事;而另一个则是将不美好的外物撕裂,把一直想要毁灭的更更不幸内在用自己的双手毁灭并拼尽全力传播给世人的故事。两书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父母的缺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指出,她的父母“旷课了,还自以为没开学”;《樱草忌》则是借叶荻梦中的林远江之口,控诉了因为自己被毁灭所以也想要毁灭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母亲。但在更深层次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讨论里男权社会,而《樱草忌》讨论了最基本的一件事——贫穷。联想起近来高考考生“感谢贫穷”以及拼多多“助力贫穷”的新闻,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咂出一丝苦味。我觉得,用高层指出的两个主要矛盾可以完美的概括——“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和“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物质贫穷导致精神的贫穷,想要拼命跳出井口却又徒劳的“井底之蛙”,最终选择了付出一切却又无谓的复仇,也就在理所应当之中了。不过反青春,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
再谈谈两位女主的人设——
叶荻:如果没有林远江,她可能会成为班级里的林远江。虽然她的父母始终没有缺位,却显得太过平庸。她是个好姑娘,爱读书,有独立思考能力,临危不惧,成绩不差,没有短板,还具有大多数人没有的优良品质,比如涉猎广泛,比如坚持。叶荻的最大缺点是太年轻,没有到达浸淫世故的年纪,却有了些可能正确但绝对不成熟的想法。万幸的是,她不是冯露葵,因为她还算乐观,并且不够完美。结尾处她认为自己一辈子忘不了林远江,这话要分两面看。一方面来说,她终究会忘记林远江,所谓的寻找“近似解”,不是林远江死去的答案,而是自己活着的答案;另一方面,林远江是她“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对象,更是是她走向成熟的引路人。
不过正如标题“叶荻,你一定不懂吧”,她到最后也肯定不明白林远江的一切,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将林远江的生死归咎于爱、恨、倦、悔、厌等情绪或者是它们的组合上。能够懂得自己的,永远只会是自己,却不一定能够是自己。就像这句话的原版,美羽对于心叶所说的“心叶,你一定不懂吧”,到最后,即使两人和解,即使美羽遇上了良人,还是没有人懂得美羽本人的思想。感情这样私人化的东西可以传递却无法传达,所以“懂得”永远都是虚妄。不过,如果你跳出窠臼,会发现所谓的懂得是可以不选择的。这个世界上所有幸福的人,都不会要求任何一个人懂得自己。叶荻在未来的某一天,终究会发现“不懂得”“不找寻解释”的美好。
林远江:偏激、固执、可怜、可恨、可悲。企图用不成熟的死去报复一个成熟的社会,同时自导自演了一部短剧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故事”,最终肯定是无功而返。她的自杀是在这个社会的助推下导致的,尽管她的意志占了主导,但终究不是全部。对我而言,真正可以接受的自杀就是身无牵挂,完全左右了自己思想的自杀。可惜的是,这是真正需要“顿悟”的东西,因为能够做到这些事的人已经全部不在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被任何事物煽动的时候,他/她的自杀就算不上是“最好的”。
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樱草忌》绝非轻小说,因为轻小说角色的属性是组合出来的。确实,文中的大多数人物复杂到难以拆解,但林远江不是他们,林远江是作者塑造出来的属性的集合体,可惜的是这样不切实际的角色让《樱草忌》本该拥有的致郁和灰暗色彩成了虚妄之物。
关于作者提到的社会问题——
亲子问题:文中没有一对完美意义上的“好”父母,却也没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那样完全缺位的父母在。即使是林远江,她的母亲也没有完全的缺位,而林远江本人的控诉,终究只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叙写。她日记中的“那个老女人”这个让人厌烦的人设,换在林远江母亲本人方面可能就是另一个尽职尽责的样子。我不敢说林远江的母亲完全没有悔过,但从她本人对于置之叶荻于死地的巨大执念可以看出,她并不觉得自己是缺位的、失职的。事实上她确实也没有,林远江提到的新居室、美国大学,可能都是她心中的“那个老女人”想要真真正正供给她的。尽管她的管教具有巨大的不合理性,以至于使得“林母”这个人设都是扭曲的,但她终究,是个合格的母亲。
至于其他人的父母和亲人,大多数都太平庸,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叶荻的外公。“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和“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的对比,初读时觉得些许突兀,读上两三遍之后便会觉得这是书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之一。外公这个没有出镜的人物,偏偏是文中最有智慧的长辈,联想到后期网络暴民对他的攻击和谩骂,悲伤的诙谐感油然而生。
网络暴力:文中的网络暴力是典型的“中国式”,先谩骂,然后带节奏肆意抹黑,到达顶点的时候吃瓜群众下场抨击“恶人”抨击社会抨击一切,少部分人开始以此牟利或者借机攻击仇人。在文章发生的年代狗粉丝和批小将还不算主流喷子群体,否则还要加上梗乱飞,反串黑和口嗨成瘾。当然,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有反转,再反转和再再反转,人们开始选边站和互喷,一如十年浩劫的缩小版。表面上看是社会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教育水平的低下,其实最终还是要落到主要矛盾上去。匮乏是一切网络暴力的成因,而主要矛盾又是匮乏的成因。
如果林远江本人的故事逻辑再缜密些,配合出演的她再入戏些,将会更好的调动起网络暴力,不过在当时的网络环境下,75天之后也会被遗忘的差不多。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放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狗粉丝的疯狂反串就能把叶荻安排的明明白白,再加上批小将的玩梗,恐怕这件事在多年以后依然会是个一出类似的事就会火热的段子。生活在一年以前前的叶荻如果真实存在,看到今天的场景,不知道会庆幸还是会感叹。
校园欺凌:在《樱草忌》中,参与网络暴力的不少人和校园欺凌的发起者都有着同样的理由——通过对一件看起来罪大恶极的事的强烈批判来消除自己本身因曾经犯错而产生的罪恶感。因此,叶荻给出的“你们为什么不和林远江做朋友”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给出答复。
需要指出的是,校园欺凌的种类数不胜数,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破坏美好事物的恶劣天性”,但细究起来,终究不同。
作品的缺陷——
1.日记部分很难找到共鸣点
很少人能切身体会书中人物的境况,但好作者能让读者无限接近这一点。对于林远江的日记部分,说实话,并没有太多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因素存在。很灰暗,很致郁,但虚无缥缈,但没有任何心灵上的震撼或者记忆中的重叠,就好像一个人指着一堵沾了血的灰墙,告诉我这是致郁,这是灰暗,够直接但不够抽丝剥茧。另外,某些桥段让我以为自己是在读《悲伤逆流成河》……
2.作品的核心不明
诚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可能是想做一个奈保尔,或者说是三秋缒,叙述但不议论。然而正是因为如此,让本书失去了核心。看简介,以为是《狩猎》一类的作品;翻开初读,以为是《时间静止的校园》;再读下去,就成了各种思想的混杂体。在《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中,你也可以找到多个核心——“顿悟”“先定论”“利己”等,但绝非像《樱草忌》一样杂乱无序,因为它们是为了“动机”服务的。《樱草忌》对于“动机”的掩盖严重不足——看完日记就能知道凶手的目的和手法,以及合理性偏低的伪解——导致了繁多核心思想的散乱交织,使得作品真正的核心无法显露。
3.不融洽
《樱草忌》犯了和《天空放晴处》一样的毛病,那就是前后的氛围微妙的不融洽。短篇可以解释成篇幅使然,但一部中篇,或者说可以成为长篇的中篇,再出现这样的毛病,有些令人失望。
前作《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经常被吐槽太过日式,我觉得这么说的人基本没有去过日本。众多日本推理小说家笔下的日本,也并非全然的真实。《当且仅当雪是白的》里的世界,应该说是架空的,是多地的混合体,却不缺少流畅和连贯。但在《樱草忌》和《天空放晴处》中,作者加入了一些中国化元素,比如129大合唱、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式消防演习等,反而让作品显得愈发不伦不类,不仅丢却了原有的连贯性和流畅性,还把架空的氛围也丢弃了。另外,《樱草忌》不仅犯了文化上的毛病,更有时空上的问题。诚然,林远江是个格格不入的“古人”,但她生存的环境就像是十几年前的社会,这也是我读日记之时想到《悲伤逆流成河》的最大理由。本身,这样的脱节是有助于表现林远江本人的人设的,但是,脱节的并不只是林远江一人。叶荻、林母等众多角色,都像是活在新社会的旧人。这样的组合就像尴尬的土味情话,将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空生硬的缝合在了一起,顺带着把架空感抹去,留下了一地鸡毛……
我相信作者的笔力和阅历足以支撑他写出更加优秀流畅复杂深刻的作品,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试错的能力。
4.对于青春小说的片面认知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自己已经不了解青春小说了,不过《樱草忌》对青春小说的诋毁还真是一只手数不过来。文中的上海杂志我个人理解成《萌芽》,在今年高考之前,我差不多看了一年半的《萌芽》。如今的《萌芽》我不敢说有多好,但多元化是肯定的,也会有林远江投稿的那一类作品的刊载。《萌芽》每期会刊登对于社会热点的讨论以及某些知名青春文学作家的访谈,而这么多年来《萌芽》也挖掘了《我们云端见》《马贼》等作品和王若虚等作家,它对于青年作家的寻找和培养,绝对是功大于过的。
至于其他的一些“青春小说”,脱离了早期的虚无和媚俗,这几年的质量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于网文写手也在努力提升自己作品的涵养,某些带有深度的思考和偏执但不偏激的论点具有非常深刻的讨论意义。
实话说,像《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样的作品,在我市的书店里,是和青春文学放在一起的,预计一下《樱草忌》,大概也是如此。不知道作者若看到此情此景,会作何感想……
作品的疑问——
1.我经常在杂志上看到投稿告示,上面一般都写着投稿后不退稿,但是三个月内未刊用/获奖请自行处理?所以林远江的原稿在落选之后不应该是属于她本人的吗?为什么可以继续刊登?
2.伪解的不合理性?
3.姚老师的推理水平为什么下降如此之快?
作品中的一些梗——
作者比我年长12岁,但我20年后的阅历可能也赶不上作者现在的万分之一。如果你读完了《樱草忌》,你会发现作者涉猎了哲学、文学、音乐、美术、galgame、anime中的众多作品,不少还是无比硬核的“神作”。
1.文学少女
林远江和天野远子除了爱读书外没什么共通之处……家庭背景也只能说是“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不过比起天野远子,林远江和日坂菜乃才是真正的对立面,一个元气max,一个孤僻冷淡;一个喜欢生活,一个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意义……最重要的是,一个喜欢契诃夫,一个认为契诃夫“没有故事”。
2.《 a far song ……》
其实是《 a far song 〜カナタノウタ〜 》,田中罗密欧《最果てのイマ》的OST里的曲子。自诩为半个田中厨的我,虽然推完了《家族计划》,也补了《人类衰退之后》和《灼热的小早川同学》,但对于《最果てのイマ》这样的硬核作品也只是闻名而未见面。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随手放个大招的作者有多么恐怖的知识储备……
3.《窄门》
为了文少去读的《窄门》,从此成为纪德的拥趸,文中林远江对于《窄门》的看法和我意外的相似,因此增添了一些对《樱草忌》的好感。
比起《窄门》,或许将林远江拉入写日记坑的《纪德日记》更值得一看。
4.《米格尔街》
奈保尔的名作,《樱草忌》提到的名著中为数不多的几本我读过的。和作者想要传达的写作手法十分相似。
5.米泽穗信
“我很好奇”是《冰菓》,而林远江讨厌的那部作品是《算计》。
6.其他
除了以上,《樱草忌》中提到了《春雪》《尼各马可伦理学》《摩奴法典》《淮南子》《请问您今天要来点兔子吗?》《阴火》《O侯爵夫人》《伊甸园》《克鲁采鸣奏曲》《春天》《梦醒之后》《歌德谈话录》《墓畔挽歌》《你往何处去》《小杜丽》《故事形态学》《辞海》《德米安》《绿山墙的安妮》《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女生徒》《哀江南赋》《天平之甍》《白色相簿2》(我自私的将情人节过生日的动漫角色当作小木曾雪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安妮日记》《魔女嘉莉》
还有我看不出的一些作品,比如在火星上划船的动漫,比如那位说“小说和香烟让时间加速流逝”的法国作家……作者涉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以至于让《樱草忌》有了一些炫学的感觉。
总结
《樱草忌》和《天空放晴处》都算不上是非常出色的作品。只谈《樱草忌》: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一样出现——故事情节难以产生共鸣,核心意义不明确,张力不够以致于结尾的梦中对峙气氛感太弱,因为“反青春”而对于青春文学带着些偏见和傲慢。亮点也是有的——尽管故事本身不够动人,但变改的文风较之前作更上了一层楼,对于人物行为合理性的编排比之前作更有说服力,行文结构严谨,呼应的点完美的扣住。遗憾的是,亮点不足以让这部作品完完全全的成功;而缺陷,可能会让作品不上不下的失败。
正如开篇所说,《樱草忌》是一本“新小说”,我们看似能将它和众多名作佳作等同,最后却只会发现它是独一份的。然而,作者在创新的时候没有办法全然抛弃旧理念,某些要素的引进又太激进,使得《樱草忌》终究只能成为一本实验性质的小说。故事性强、反转惊人、高潮迭起,和它都沾不上边。唯一值得称赞的是结构,可是结构,恰恰是这本“新小说”为数不多的守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