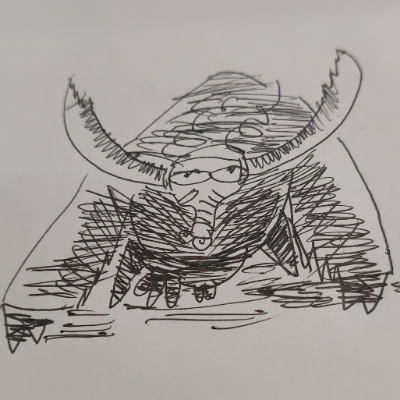《东京札记》:字字写日本,处处是中国
刚读完葛兆光教授的新书《东京札记》,借着这本书得以窥探当今日本学术界的全球史观, 通过葛教授对中日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反思,让我读到了而很多有意思且深受启发的观点,比如在20200115这一篇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日本因为是二战亚洲策源地,在经历过彻底战败后,使得日本社会可以公开讨论“爱国”是否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理所应当的自然感情,围绕着这一话题区分了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市民祖国和建立在出生、血缘、民族基础上的自然祖国,因此日本对二战的记忆混杂了否定性的政治判断和留恋性的情感记忆。 在日本,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是某个寺院的信众,死后一个人的灵魂会去该寺庙报道,这个寺庙就是这个人最终归宿,这就是日本国教-神道教的“檀家制度”。在神佛习和这一点上恰好和我们当地的风俗非常相似,虽然很多人信奉佛教,但依旧认为自己的灵魂归当地庙宇掌管,而这些庙宇供奉的也不是神佛,而是“老爷”。 通过谈论神道教,葛教授又引用了尾藤正英所著的《日本的国家主义:“国体”思想的形成》一书关于探讨的日本国体如何形成的观点,解释了日本这个神道教国家,自形成国家以来,天皇通过举行祭天敬祖的仪式,把忠孝道德观散播全国,浸透民心,让“以忠贵贵,以孝亲亲”成为无需言说的价值观,让国民对天皇的自发性服从。 而这种实现了国家紧密统一性的体制,丸善真男所著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指出正是这种国体,让日本在大政奉还后的明治、大正与昭和时代走向了军国主义。日本国民对国家的自发协力,让国家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学术和艺术的创作自由必须依附在这种强有力的价值判断实体上,而这种依附绝不是表面的附随,而是内心自觉且真诚的相信政府提倡的价值。通过丸善真男的论述,可以推断正是国民对日本帝国的无条件信任,所以帝国的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甚至要为此进行辩护。因为“国体”的神圣性,让任何有关国家的讨论,无论历史、政治还是文学艺术,都立即变成了政治问题。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二战后,盟国之没有废除天皇制,也是出于战后既要维系住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又要避免盟国深陷援助,同时还要翦除军国复辟的多重需要,于是空降和平宪法,采用让所有国民效忠于一人,余下众生皆平等,但同时用议会架空君权防止独裁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才保证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得以百家争鸣,让极端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国体丧失了绝对性,让自由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体。能够理性区分nation、country和state,这可是衡量一国国民是否已进入文明世界的的基础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