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季风读书 | 李奕潮评《杀戮季节》
对于不熟悉印度尼西亚政治的中国读者来说,1965—1966的大屠杀可能是一团模糊的黑暗。在许多中译本读者的语境中,上世纪末“五月暴乱”的记忆,与这场大屠杀已经潜移默化地交织在一起。印度尼西亚背弃了教科书所预设的历史发展方向,废黜了老朋友苏加诺大哥(Bung Karno),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走向了反动的黑暗。而这个反动过程的代价是,“优越”的华人被“未开化”的印度尼西亚土著民杀戮、驱逐和强制同化的神话,在“五四”以来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基底上留下了一个深坑。苏哈托“新秩序”政权血腥的开端,貌似能与其倒台前的暴力相呼应,共同建构出一个闭环的故事。这些创伤还没有得到严肃的解释,已经被现实的发展利益所覆盖,被纳入不可言说的领域。“深坑”边上带刺的铁丝网、标有“政治”字样的告示牌提醒:我们需要绕开它,以便进入到全新的历史进程当中。然而,创伤经验所依据的时间观不同于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创伤的过去拒绝成为历史,因为它还在以某种方式留在当下。很少有读者知道,当修筑高铁的中国团队来到爪哇,印度尼西亚最负盛名杂志之一的《时代》(Tempo),以“工人”(buruh)一词称呼他们,而这个词语带有左翼运动的隐喻;高铁开通的日子(10月1日),巧合地遇上了大屠杀托词的开端,被反共势力所纪念的“潘查希拉奇迹日”。近些年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一些作品,已经展示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关于大屠杀的创伤故事。许多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或许还观看过纪录片《沉默之像》,同情于大屠杀受害者家人的痛苦;抑或折服于印度尼西亚小说《人世间》(Bumi Manusia)的精妙构思,好奇作者传奇的布鲁岛流放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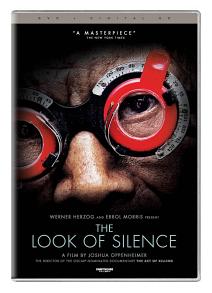
The Look of Silence. Directed by Joshua Oppenheimer. Drafthouse Films, 2016. DVD

右: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人世间》,罗杰、对方重校,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
值得振奋的是,本书不仅论及了这些作品,还给予了相关问题所对应的严谨解答。不过,与上述作品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关注旨趣迥异,《杀戮季节》力图系统性地展现一幅1965—66年大屠杀的全景图像。本书雄心勃勃地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全国的大屠杀,及其在后续数十年中的长期影响;所提炼出的大屠杀“国家模式”,使之成为学术界对该事件宏观研究的开山之作。因此,《杀戮季节》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认为是一次勇敢而意义重大的尝试。它奋力穿过了铁丝网的阻挠,遍体鳞伤地在这个坑上架起桥梁,试图用一种学术的理性方式,去部分重塑中国读者对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认知。这需要摸索权力和不可言说的边界,与过去的创伤进行大胆的对话,并且在认知、批判的过程中走出它的阴影,真正地面向未来。耐心地阅读完整本书的读者可以看到,这恰好也是《杀戮季节》重要的现实关怀之一。该书不仅以英语出版,还以印度尼西亚语出版,直接面向它所剖析的社会。最后四章基本以编年的顺序进行延伸,重点探讨了创伤的问题。杀戮之后还发生了大规模拘捕、流放,而1970年代末这些流放者被释放之后,仍然面临着严酷的社会限制、规训和惩罚。侥幸活下来的个体继续接受肉体上的折磨,长期的关押、流放和强制劳动;而死者的亲人必须忍受亲密关系被摧残、被社区污名化等后果,这是双重的精神创伤。“新秩序”结束之后这些措施土崩瓦解,但是“专业集团”势力仍在,追寻真相与正义的尝试仍然面临重重的阻力。这些阻挠所采用的托词不过是陈词滥调。《杀戮季节》系统地揭示了“新秩序”的三十二年间,该政权已经建立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宣传内容。这些关于“九三〇运动”和合法化大屠杀的神话,使得犯罪者能够说服自己是在“拯救国家”。这解释了为何只有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人才会受到创伤,而犯罪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毫无悔意。作为在康奈尔大学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兼人权事务专家,罗宾逊还参与了对东帝汶民众(同样是印度尼西亚军队暴力的受害者)的救助活动。这些鲜活的实践经历,推动构筑了本书的另一个现实关怀。即从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全球性的意义上,反思这些暴力的遗产,以及令人寒心的沉默和无所作为。在《绪论》中罗宾逊就提示读者,沉默和不为人所知是这场大屠杀突出的特点。第七章分析了大屠杀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在美国、英国外交和情报系统的帮助下,军方获得了有助于进行搜捕、屠杀和夺取政权的物质资料,并且建立了心理战机制,持续地鼓动暴力。在舆论宣传中,英美很可能还与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西德在内的盟友进行了协调。它的镜像是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友的协调。在1966年末大屠杀结束之际,西方(美国)的记者们深入了印尼,然后有意无意地复述凶手们的托词。简而言之,一些西方国家并不像他们所自我辩护的那样,是“九三〇”事件后,印尼国内血腥政治事件的无辜旁观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一种隐秘而有效的方式,干涉某个亚非拉国家的内政。第四章也在冷战对抗的框架之中解释了隐秘行动的逻辑。这个框架并没有超出读者们的常识。然而,对于希望了解一场大屠杀的历史的读者来说,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是犯罪者?谁是受害者?犯罪者如何进行了杀戮?这是《杀戮季节》的核心内容,也是最挑战大众常规认知的部分。《绪论》鲜明地提出,大屠杀本质上是政治行为,并不是社会经济或文化冲突的“自然”产物。第六章论证了军队在大屠杀的关键作用,在国家层面上,宣告了“地方冲突论”的破产。杰斯·梅尔文(Jess Melvin)同年出版的研究,提出了以军队为核心的“两阶段”框架。第一阶段是,受军队支持的民兵,对特定左翼人士进行公开的残忍处决;而在大众不可见的第二阶段中,大批惊恐的左翼人士寻求官方庇护,反倒被早有预谋的军队集中起来秘密处决。两本书分别从宏观、微观视角入手,共同推翻了宗教矛盾、土地改革和虚妄的“民族性格”导致了大屠杀等迷思。这些谬论不仅是对大屠杀的片面理解,还为自诩“中立”的军队提供了良好的伪装。对于受害者,第五章也毫不隐讳地批评了“一种常见的错误观点”。绝大多数的遇害者并非华人,被牵连者并非因为他们的阶级或种族,而是因为他们的(或是被指控的)政治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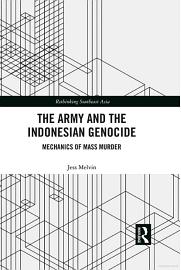
Melvin, Jess. The Army an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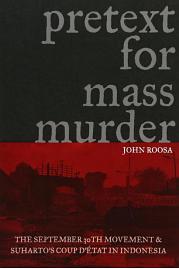
Roosa, John.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
在读到这些激动人心或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段落之前,罗宾逊还冷静地提醒读者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场事件的指称——“九三〇运动”——需要受到批判。十月一日当天确实发生了一次政变,它造成了极其有限的伤亡,而对于政变的歪曲解释成为大屠杀的托词。它不仅掩盖了随后发生的恐怖,还暗含着“受害者有罪”的立场。这场政变背后存在着数种相互冲突的叙事,其中约翰·罗萨(John Roosa)的解释具有相对最佳的说服力。尽管这些解释都试图讲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读者还是不得不面对异国的姓名、特殊的缩写和难懂的术语,这些都需要最初两章的历史叙事作为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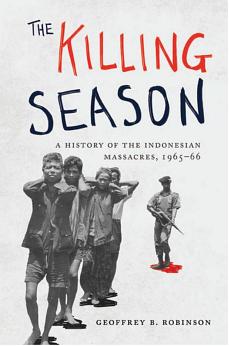
Geoffrey B. Robinson, 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 1965-66,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尽管《杀戮季节》的志向在于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它仍然以优雅的文风和现实的关怀,谦逊地面向普通读者进行写作。然而,可以预想的是,一些中译本的读者或许会失望地发现,中文语境中关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创伤,只是以一种边缘的形式在书中出现。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位。因为历史学家并非在真空中重建过去,而是面对特定的读者。原书被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人权与反人类罪”系列之中出版,暗含超越国家与族群的界限,进而面向全球人权保护的普遍关怀。尽管原始的历史资料并不直接支配重建过去的方式,但是它的能动性使其能够对为多种历史书写提供空间。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杀戮季节》中译本将超出它在学术上开创性的影响力,而赋予关心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中国读者与创伤和解、与神话搏斗的勇气和智慧。参考文献Roosa, John.Buried Histories: The Anticommunist Massacres of 1965-1966 in Indones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20.Schaefer, Bernd, and Baskara T. Wardaya, eds.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Melvin,Jess.The Army an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8.Xie, Kankan.Review of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 by Geoffrey Robinson,Newbooks Asia, 2019.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uHE0PXYz1qxd60upeB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