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olution, Revolution never chan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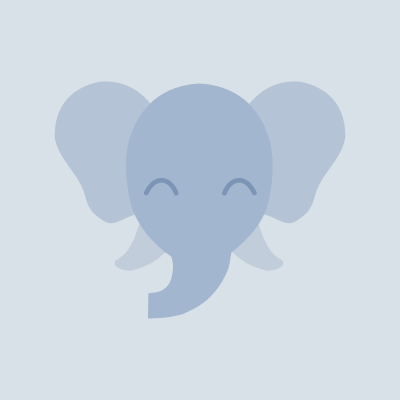
共和国史是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一个唯意志论的民粹主义者通过一系列斗争将党改造为民族共产主义政党,战胜了腐朽的国民政府,建立了共和国。
他对党员的道德预设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演化为“特色不断革命”并在前三十年内展现出滑稽的姿态——“一穷二白是好事”“党的领导者反对党本身”“以个人崇拜压制党内官僚阶级”,并与主要是热月党派反对者和支持者们鏖战疆场,也因外部因素和决策失灵酿成大规模饥荒和经济衰退,反而使热月党人得以复辟。
十年浩劫初期,热月党人首先对脆弱的知识分子加以迫害,认为如此这般方能“顾全大局”;他期待新一代能再造共和,但接踵而至的社会动荡让其意识到“党已大而不能倒,而年轻激进分子无法托付政治理想”,于是便迅速右转,抛弃了绝大多数之后被屠杀或下放从而蹉跎岁月的左倾信徒,再次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者、雅各宾派热月党党魁,甚至事实上“二共”的开创者。
迈氏认为开创者个人便可决定运动的命运和限度,人民意志无足轻重,其打击官僚阶级的个人崇拜手段也在十年浩劫中盛行,最终成为先祖崇拜的一部分;而其对民主政体的疏离,企图通过群众而非体制达成社会主义愿景也是前三十年动荡的滥觞。
开创者的努力酿成无数悲剧、未能从根源上摧毁官僚阶级和他们的特权、乃至耗尽了其思想曾有的巨大创造力,却也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卓有成效的打击了不平等现象、更为未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迈氏隐晦地点出继任者实际上扮演了“摘桃子”的人,开创者偏重三农、大力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未在前三十年显现,却为继任者上任之初农业大丰收的主要原因,而其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影响不大,这样的进步也未能在制度影响下持续,至于其反对农业集体化的“一刀切”手段,恰是开创者思想中的缺陷部分。
这位继任者凭借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夺权,但转瞬便背叛了昔日盟友,推行官僚资本主义和政治专制策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让党化身资产阶级的代表。
该时代的一位政治人物因试图遏制该趋势而被迫远离政治舞台,最后仓促离世;另一位本是依靠该趋势牟利的官僚资本家,他本人反而因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鸿沟导致的动乱成为殉道者,累忝殊荣。
继任者在动乱发生三年后重申改革开放,使经济回归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让通货膨胀率再次激增,西方媒体对其的报道经历了“改革者→刽子手→改革者”的轮回,正如其在十年浩劫中的“三落三起”。
第三代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舆论收紧,同时淡化阶级叙事,倚重民族主义,凭借前任指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使国家繁荣富强”彻底将激进的革命理想从保守的民族主义中剥离,把人民的爱国情推向高峰。
迈氏在最后敏锐地预言“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已由理想变成了威胁,支持社会主义则必然要对抗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并谨慎乐观地估计沉寂已久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先锋队,扮演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到了今天,他们似乎已成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而奋斗终生。
迈氏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观也颇具洞见,他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本身并不能够创造历史,必须和其他阶级联合并抓住机遇成为意见领袖,才有可能依照理想改造社会;十年浩劫中的知识分子先是被热月党人攻讦,最后沦为砧板上的鱼肉,而任何一派都可拿其开刀;之后的知识分子先是扮演了继任者的盟友,遭受背叛后成为社会的反对者和动乱的代言人,但其固有的精英主义立场使得未能与工人阶级联合,成为“特色团结工会”,宏大的政治理想也最终幻灭成泡影。
迈氏以鲜明的左翼史观写就该书,在肃反运动、市场经济、秩序主义等方面有不少偏颇之处,而正如评论区的某些先生所言,其在解读重大历史问题的发生时也可能落入了预设的窠臼,精彩地错过了某些偶然和必然的诱发因素,但其依然是一本大体上理性客观,且有众多精妙论述的史学著作,我想每一位读完此书的人,都会重新审视共和国的历史,并发现历史与真实间微妙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