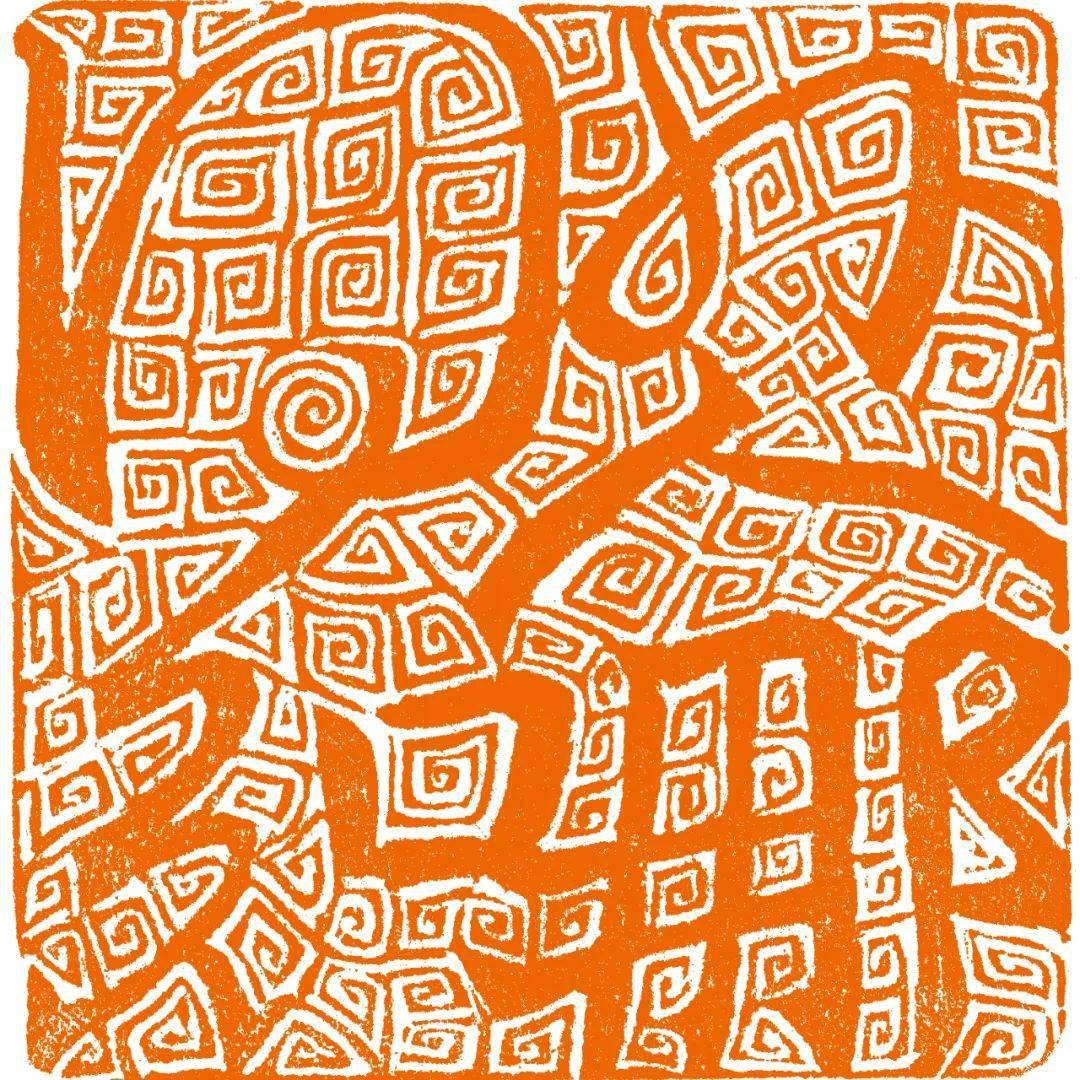梦醒子:一个从未梦醒的人
这本书反映了一个传统文化统治中国晚期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在他的生命展开过程中,基本上是一路低走的悲剧性故事。这种悲剧,不像鲁迅笔下那些人物来得激烈,但正由于其非虚构性而格外具有悲剧力量。
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关键在于刘大鹏对儒学思想的无条件服膺,而这这种思想与现代性的深刻变革和背后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儒学是以一种宗教的姿态来指导刘大鹏的日常生活的。他需要每日焚香沐手,虔诚地书写日记,每日三省其身,躬耕,遵循道德约束,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君子的嘉名。与别的宗教相对应,日记的书写对刘大鹏而言,有自我道德净化的意义——这种方式和佛教的打坐念经很相似,几乎是一种宗教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刘大鹏在日记的书写中,时常效仿他的精神偶像曾国藩,“幻想有朝一日日记得以出版”,这使得日记的真实性存疑,至少是部分存疑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说法来看,这种美化倾向肯定是存在的,他在叙述策略上有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有道德形象塑造的考量,但无论如何,这都让刘大鹏更为真实,这些因素也使得日记这一特殊体裁更具有被诠释的魅力。
八股科举,这股生发自儒学内部的形式,在刘大鹏这里,已经演化成了一种阻碍自己精研儒学、虚妄害人的毒物。从私塾到书院,从刘午阳到杨深秀,一路以来他所经历的儒家教育都是轻视八股科举的,这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命运,也给他带来了长久的痛苦——直到他自以为自己梦醒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追求方向,但是实际上,他始终不能真正摆脱和当下世界格格不入的痛苦,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从他的梦中醒来。
文中写道:“他感觉教书足以摧毁人的道德自律和雄心壮志,凡是真正志在成功的人是不会设馆教书的。他自己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暂时养家糊口,若一生以此为业则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刘大鹏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他的大半辈子最终都扮演着一个教书先生的角色,他就这样放弃了年少的大志,并且在一次“梦醒”之后完全合理地说服了自己。尽管在人生的后半期,他颇感自得、颇觉舒适地成为了一个“德高望重”、关心地方性事务的“乡绅”——并且他靠此常常获得一种虚幻的快感,一种因为自身价值观在当下社会依然有效的满足感,当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话语权已经丧失后,这种虚幻的快感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说,他其实一直在梦中,一直未醒,他不过是从一个梦掉入了另一个梦,在这些梦的背后,都只能看到无可奈何的底色。
不妨来看看当时国家的上升通道:科举;买官;新式学堂、留洋,致用之学。其实买官已经说明,国家并不相信科举所选拔出的顶级人才所带来的价值能和一个买官者所提供的资金相提并论。而刘大鹏的悲哀之处正是在于无法或者说无意认清时局,无法介入当下,受困于儒家修身哲学。他始终顽固地相信,儒家那一套行为规范能够改善每况愈下的国势,这种局限性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悲哀。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他自己一直活在梦中,他并没有感受到我们所感到的悲哀——他不知道子女分家、儿子疯掉、吸鸦片,他最终做到了在自己的梦中怡然自乐。达到这种怡然自乐,正是他对儒家的坚持所成立的,一旦他发现自己完成了某种儒家要求、或者接近了儒家先贤,即便这种接近具有某种表演性,但正是在这种对先贤的模仿/表演/接近中,他就被赋予了快乐。
儒家思想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也无法起到道德约束和改造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刘大鹏一生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都无法对他的这种近乎苦修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因此他的子孙无法承袭他的主张和思想并非怪事。刘大鹏可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所遭遇的精神晃动折射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这一特殊时期所经历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