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50-254 读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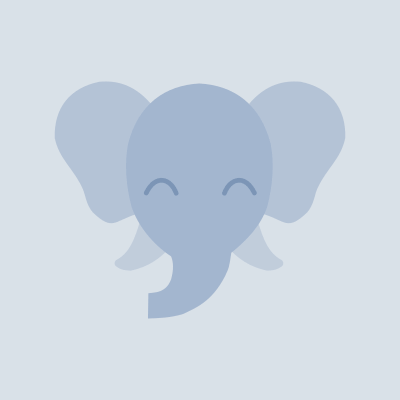
通过温柔之消隐与失神恍惚,主体并没有将自己投向可能者的将来。尚未存在并不列于同一种将来之中,在这种将来里,所有我能实现者都已经汇聚眼前,都已经在光中熠熠生辉,都呈交给我的预期并激发起我的权能。尚未存在恰恰不是一种只会比其他可能更遥远的可能。
先梳理一下上文联系到这里的一些线索:
- 首先,爱人(女性)的临显(温柔),是以一种虚弱的姿态;
- 爱者在爱人的这种姿态面前的运动,是同情和抚爱;同情,即同情其虚弱,为他人而怕,对他人施以援手(接近于伦理关系(欲望)?这里是在强调爱人-女性有“他者”的这一面向);抚爱则具有一种心满意足(似乎接近于“需要-满足”?当然这里的需要所需要的不是物(但也不是人,p249))。所以爱,截至目前来看,好像就介于欲望与需要之间。不是一种价值上的居间,而是一种“机制”上的“居间”;这看上去比较符合我们对于爱的流俗意义上的考察(爱包含了精神性维度与生理性维度),列维纳斯也是由此种理解出发,并在后文进一步的阐述中逐渐澄清了这种误解。
- 抚爱是感性,但不是普通的感性,它超越可感者;抚爱表达着爱,但无能诉说,于是渴望着表达本身;这种渴望又是不断增长的,以至于走向了追求超逾存在者,甚至是未来的存在者。
爱人的临显→激起爱者的同情抚爱→抚爱表达爱,却无能诉说,于不断增长的表达的渴望中,走向了未来的存在者。也就是,爱人的临显把爱者引至投向一种未来。
这段中想澄清的就是这种未来并不是可能者的将来(注意将来与未来的区分——未来作为一种绝对的将来)。可能者的将来是一种在可预期的时间中能够实现的将来(“我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种“观念或计划”(p249)。后面这句就格外体现了这一点,一种可预期的将来就是我可以去理解和筹划的,它激起的是我的权能(对应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而尚未存在才是爱者投向的那种未来。它与可计划的将来的区别,不在于我计划不到(如“比其他可能更遥远的可能性“所暗示),而在于它压根就不作为一种“我的可能性实现”出来(类似生育——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我筹划出来的,是“我的可能性”)。
抚爱并不行动,并不掌握诸可能。它所打破的秘密并不像一种经验那样对它进行告知。秘密打乱了自我与自身、自我与非我的关系。一种无形的非我把自我挟裹到一种绝对的将来之中,在这里,自我摆脱自己并丧失其作为主体的姿态。自我的“意向”不再朝向光,不再朝向富有意义者。
抚爱并不接近于“掌握“与”摸索“。如果我们把摸索理解为一种“打破秘密”的话,那么它所打破的秘密,就好像是事物的操作原理一样,它被打破之后,就呈现为经验向我们进行了告知(试想钻木取火的例子!在我第一次发现钻木可以取火之前,它呈现为一种大自然的秘密。但当我通过摸索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它就形成了经验并向我们传递了知识。)。但抚爱打破秘密是在它作为一种揭蔽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它所打破的秘密却又是“完好无损的”(p249;女性本质上可侵犯——打破秘密,又不可侵犯——秘密又是完好无损的,它什么也没有向我传达)。与上面那种秘密相对,这种秘密不向其告知任何东西,还“打乱了自我与自身、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其中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在249页中提到:“在抚爱中,身体已经从其形式本身中裸露出来,以便作为爱欲性的裸体呈交出自己……身体脱离了存在者的身份”;“这时候的肉体并不与“我能“的本己身体混而为一”;在这里列维纳斯需要展开的就是秘密如何打乱“自我与非我”的关系。这里的“一种无形的非我”指的就是女性,所以后文探讨的就是爱情(爱者与爱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被挟裹到了一种绝对的将来之中(未来);在绝对的将来中,自我就摆脱了自己并丧失了主体的姿态:自我就不再朝向一种仅仅是认识活动,而打开了向外的视野。——以上部分列维纳斯想要澄清的是抚爱之区别于感性:其不仅仅只有一种内在的视野。后面就进一步展开了这种“朝外的”视野(涉及到这种朝外的视野与对绝对他者欲望中那种朝外的视野的同与异)。
整个的爱情,是对被动性的感同身受,是对受苦的感同身受,是对温柔的那种消隐的感同身受。它死于这种死亡,承受着这种受苦。作为感动,作为没有受苦的受苦,爱情已经在心满意足于其受苦之际得到安慰。感动是一种心满意足的恻隐,是一种愉快,一种转变为幸福的受苦——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快感在爱欲性的欲望中已经开始了,并且时刻保持为欲望。快感并不是前来填满欲望的,快感就是这欲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快感不只是急切的,而且是急切本身,而且还呼吸着急切并急切得窒息,为急切的终点所震惊,因为它一往无前却不走向一个终点。
上面讲了抚爱,下面则进入到同情。所谓爱者在爱人的虚弱面前的运动之同情与抚爱,其实也根本不是两种运动(只是我为了方便解释暂时做出的划分,提示爱欲流俗意义上理解的两重维度),列维纳斯找到了“快感”把这两种运动又统一起来。“作为感动,作为没有受苦的受苦,爱情已经在心满意足于其受苦之际得到安慰“。我同情(感同身受)于受苦,但我本身没有受苦,也就是一种没有受苦的受苦;在这种同情中,我又得到安慰因而是心满意足的。用这种方式,两种运动就被联系起来了。幸福的受苦是快感,也就是说,在爱人的虚弱面前,爱者的运动是“快感”。
后面几句澄清这种快感与欲望的关系。据此可知,在需要和欲望之间,我之前谈到的所谓“快感的居间”就并不是一种居间,它其实就是欲望。它根本上不同于需要的那种填满就可消除的机制(正如我会吃饱),而是与欲望一样,感到一种急切,却总也走不到终点(女性保持其隐秘),时刻保持为欲望。但它毕竟又是一种“爱欲性”的欲望,它的一些特殊之处在后文得到展开。
快感,作为亵渎,把被遮蔽者作为被遮蔽的予以揭蔽。于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就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实现出来,这种局面对于形式逻辑来说,似乎源自于矛盾:被揭蔽者在去蔽中并未丧失其神秘,被遮蔽者并未被解蔽,黑夜并未散去。去蔽-亵渎处于羞耻中,即使它具有无耻的形态:被揭蔽的隐秘并没有获得被揭蔽者的身份。在这里,揭蔽主要意味着侵犯一个秘密而非解蔽一个秘密。侵犯并没有从其鲁莽中恢复过来。亵渎所具有之羞愧使得那本来应当已经对被揭蔽者加以探究的双眼垂了下来。
快感作为爱欲性的欲望揭示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揭蔽但被揭蔽者没有被解蔽。就好像被揭蔽者永远是无法穷尽的、有所保留的、在逃避的,永远保持其神秘。这种永远有所保留的状态就是一种羞耻,而试图去揭蔽去触碰去抚爱,就是一种亵渎一种侵犯。这种关系就保持着侵犯但又始终没有解蔽秘密。于是那对被揭蔽者想要进行探究、理解(侵犯)的双眼垂了下来,也就不再用一种认识的方式,一种思的方式去理解这段关系。(这里已显露出与伦理关系的不同)
爱欲性的裸体言说着那难以言说者,但是难以言说者并不与这一言说分离,好像一个陌异于表达的神秘对象与一种寻求对它进行确定的清楚明白的言辞是分离的那样。“言说“或”显示“方式本身在揭蔽的同时又遮蔽,它既言说不可言说者又使之沉默,既搅扰又激发。“言说”——不仅所说——是歧义性的。这种歧义不是在言辞的两种意义之间上演,而是在说话与放弃说话之间上演,在语言之有所表示与虽然沉默但仍然隐藏着但色情之无所表示之间上演。
这段展开讨论了爱欲性的欲望与欲望(女性与他者)之间的不同。不同在于爱欲性的裸体所表达的是一种无所表达,也不仅仅在这种所说的意义上它表达着难以言说者,而是在说话与放弃说话之间上演着这种歧义性。它难以言说,但又无法与言说活动分离。阐发地讲,就是女性是特殊的,但终究还是他者(面容在与女性的关系中同样是基础性的,尽管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这个他者不表达自己,反倒是逃避了。它所表达的就是无所表达,不提供任何含义,保持着隐秘性。也因此与女性的关系终究不同于一种此前颇多阐述的伦理关系。
女性呈示出一种超逾面容的面容。(女性)爱人的面容并不表达出爱欲所亵渎的秘密——它停止表达,或者如人们更愿意说的那样,它只表达这种对表达的拒绝,只表达话语和体面的这种终结,这种对在场秩序的粗暴打断。在女性的面容中,表达的纯粹性已经被快感性的歧义所扰乱。表达转变为不体面,不体面已完全近乎歧义,歧义之所说微乎其微,已是嘲笑与揶揄。
这种新的关系被列维纳斯形容为“女性呈示出一种超逾面容的面容”,这似乎在价值(?)层面上得到了肯定,好像这种关系更加地具有一种超越性。女性的这种拒绝表达终结了话语(很好理解),也终结了体面。不体面就是对于“在场秩序的粗暴打断“;而在场秩序则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人的表达所要求的那种始终在场(不在场则不是真正的表达,只是作品)形成的伦理关系,他人的表达为伦理关系奠基。这就是所谓的“在场秩序”——基于表达形成的秩序。而女性的不表达显然就终结了这种秩序,似乎女性所要求的并不是一种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它甚至嘲弄那种伦理关系,它“另有所图”。
在这个意义上,快感是一种纯粹经验,一种并不滑入概念的经验,一种始终保持为盲目经验的经验。亵渎,对作为被遮蔽的被遮蔽者的揭示,构成一种不可以还原为意向性——它甚至在实践中都是客观化的,因为它没有离开“数与存在者“(的领域)——的存在典范。爱并不被还原为一种混有情感元素的知识,(即便)情感元素会为知识打开一个未曾预见到的存在层面。爱并不掌握任何东西,不导致概念,它不导致(任何什么),既没有主-客结构,也没有我-你结构。爱欲既不作为一个确定客体的主体实现出来,也不作为一种朝向可能的筹划实现出来。爱欲的运动在于向着超逾可能处前行。
这段是对此前讨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正是因为女性表达着无所表达,我的快感经验就没有概念内容,就始终是盲目的。尤其区别于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的表达始终溢出我思。那绝不是一种没有概念的内容,而是一种无限的溢出。而与女性关系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逃避让这种关系构成一种不可以还原为意向性,不可以还原为知识的关系。(仿佛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我思不是思,因为它不断溢出,我无法像思一个对象那样思他者;在与女性的关系中,我思不是思,因为它什么都没有传达给我,我思的对象是空。)爱不掌握任何东西,不导致任何东西,它的运动是向着超逾可能处前行的。——从第一段到这里,列维纳斯从投向“不是可能者的将来”开始,落回到一种“超逾可能”,在看似重复之间已有所推进。
爱欲性裸体的无所表示并不先行于面容的有所表示,就像无形质料的晦暗先行于艺术家的形式那样。由于面容的纯洁的裸露并不消失在爱欲性的裸露癖中,所以爱欲性的裸体在其自身背后已经拥有形式;爱欲性的裸体来自将来,来自一种这样的将来:它所处的位置超逾了诸种可能闪烁其中的那种将来。面容在泄露中一直保持着神秘与难以言传;这种泄露恰恰通过它的越界的过度而证明自己。唯有那种拥有面容之坦率的存在者,才能够在色情的无所表示中对自己予以“揭蔽“。
这段的关键在于,爱欲性裸体不能理解为一种原初事件(原初事件仍是面容)。所以“爱欲性的裸体在其自身背后已经拥有形式“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爱欲性裸体的呈现中也是有面容的泄露的,它并不先行于面容的“有所表示”。反而恰恰由于面容的泄露(有所表示),爱欲性的裸体的无所表示才得以可能。
后面列维纳斯对关于表示的要点进行了回溯,简单概括一下重点:
- 表示的最初事件发生在面容中;
- 面容的表示先于意义给予,有面容才有意义给予(面容放射出光,光得以被看到);
- 为了作为思想意向之相关项的意义现象能够浮现出来,人必须已经为他人而在——必须实存而非仅仅努力工作;也就是说,为了有意义必须进入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在列维纳斯这里就是为他人而在),不是“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只是在留下“作品”,作品中的自我反倒是在呈现中撤出的);而是要实存,要进入到关系中,也就是为他人而在。
- 为他人而在,就是善良;我实存的方式就不只是为自我的实存,这一事情构成道德本身;道德始终不能摆脱对他人的认识。
面容既不像覆盖着内容的形式那样、也不像一种图像那样熠熠生辉,而是像在其背后不再有任何东西的原则之裸露。死了的面容变为形式,变为死者的面膜,它被展示而不是被看到,但恰恰因此它不再显现为面容。
重申了面容作为最原初的事件,背后不再有任何东西(对比前面提到爱欲性裸体在其背后已经有形式)。而死了的面容变为形式,不再在场,只剩覆盖内容的形式,也就不再构成面容。后文关于美的形式的讨论与此处有呼应的地方。
下一段中列维纳斯就对刚才所提及的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加工。如果说上面一段是从我→他人(我接受他人的表示)的这个角度去说明的,后一段则跳出了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外在性把存在者规定为存在者,而面容的表示就取决于存在者与表示者本质上的一致。表示并不是被添加到存在者上。进行表示并不等于把自己作为符号呈现出来,而在于表达自己,就是说,在于亲自呈现出自己。符号的象征表示已经预设了存在的表示,即面容。在面容中,卓越的存在者呈现出自己。
既然面容的临显展示为外在性的本原,外在性是有所表示本身。那么我们跳出“接受他人表示”的这种视角,去理解表示者和表示的关系时就得到以上的结论:进行表示就在于表达自己,在于亲自呈现出自己。而说明这点的目的在于讨论面容的表达与身体的关系。此段中列维纳斯只简单带过一句:“而整个的身体——一只手或一次垂肩——都可以作为面容进行表达”。就是说面容不可以仅当成一种形象去理解,且并非只有“面容”(狭义)才可以表达,“身体”当然可以表达(形象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身体的表达。但这里的身体也当然不仅有形象上的意思,而是在指向之前讨论的那种爱欲性的裸体。也就是说爱欲性的裸体中,面容也不会消失,女性也始终是他者,虽说我与女性的关系不同于与其他他者的伦理关系。)本段后面的部分又折回到他者的抵制,他者的伦理诫令。这一不可谋杀的诫令与爱欲所亵渎的神秘看似相对立:在面容中,他人表达出其卓越和神圣的维度;而在女性状态中我似乎亵渎了这种神圣,既然女性仍然是一种他者(在它的面容始终不会消失的意义上,女性始终是他者;但它也是”自我亵渎者“)的话。列维纳斯后文就主要解决这一对立。
但是不敬已以面容为前提。元素与事物处在尊敬与不敬之外。为了裸露可以获得色情的那种无所表示的特征,面容必须已经被看到。女性的面容把这种光明与这种阴影统一在一起。女性是这样的面容:在这里,昏暗包围着并已经侵入光明。爱欲的那种表面上非社会性的关系将具有一种对社会性的参照,即使这种参照是否定性的。
之前我们提到:
- 女性终究是他者,它的面容并不会消失(于裸体中);
- 在爱欲性的裸体背后又已有形式,并不先于面容的表达;——并非一种原初时间,而是需要面容作为前提
- 但女性所要求的又不是一种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女性的面容又不具有面容的那种对伦理关系的要求
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究竟指向什么?在这里列维纳斯终于给出了答案:面容是前提,爱欲要求的非社会性的关系不是原初事件,而是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性的参照,而且这种参照是否定性的。“包含了对社会的参照”解答了面容为何不会消失以及为何构成了一种前提,“否定的参照”则解答了女性要求的关系为何是不同的。在这种参照中,“无所表示置身于面容的有所表示中”,“面容的纯洁或体面处于那仍被压制却已经近在手边并充满鼓励的淫秽的边缘“。这种参照就是女性之美的本原事件,是美在女性那里所具有的那种卓越意义的本原事件。这才把前文的诸多线索真正串了起来。
本段后面的部分着力批判了艺术的美。他认为艺术的美并不是一种本原事件,而只是一种形式的美;美在女性那里的神秘、深度、眩晕变成了艺术之美中“平静的在场”,变成了无根的、没有深度只有表面的,也因而失去了其神秘。正如在前文提到的死了的面容仅仅是面膜、形式一样,这种美恰恰就失去了激发它想表达的美,只是轻飘飘的优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