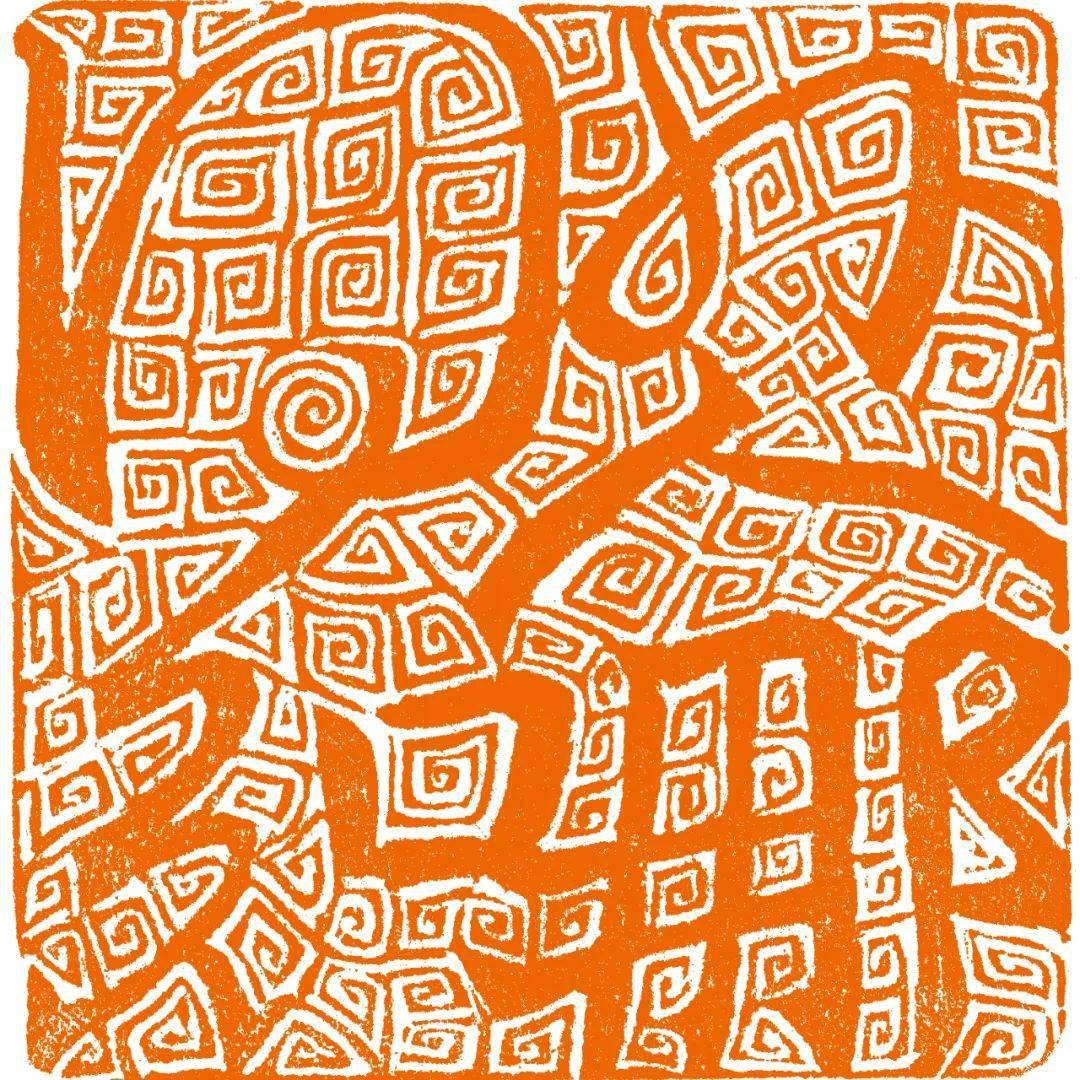《野草》阅读笔记
《题辞》
野草这个词的含义,折射了鲁迅的心境:他要让那些过去的生命死亡,用这死亡的生命来滋养他,给他以新的生命。尽管他也知道,他的这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不是乔木,仅仅是野草罢了。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他是一样的坦然,甚至,他也希望这野草能够早点死亡,因为他相信,他的死亡也能滋养下一代。
《影的告别》
鲁迅自己该去往何处,他不知道,他彷徨无措,实在不行,那就“在黑暗里沉默”。“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因为人都向往光明,而鲁迅则觉得那光明中有他所不喜欢的人存在。“我常常觉得唯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绝望的抗战,偏激的声音”。
《求乞者》
求乞者,没有尊严可言,也没有真的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存粹是无法接受那痛苦的生活,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是真的勇士,他要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他却觉得,他也逃不过求乞的命运,也将被人所看不起。这是他的悲哀和他的颓唐,他那痛苦的无处消遣的心境。
《我的失恋》
鲁迅很爱用猫头鹰这个意象。
原来是闹着玩的,讽刺而已。
《复仇》
“生命的大欢喜”,是生命的极致状态。性爱的一霎,死亡的瞬间。鲁迅歌颂生命的大欢喜,正如刘小枫所言,是对“生命力”的歌颂,和达尔文主义、进步论相关。杀戮者因杀戮而获得生命的大欢喜,正是瞧见了生命的力量,杀戮、复仇,是一种替代,一种转移,放掉他人的血,而“灌溉”了自身,人在复仇中获得力量和成长,那是对旧的毁灭,采取的极端方式。而正如鲁迅对自己的判断,这杀戮者迟早要被别人杀戮,而社会或许便在这过程中得到进步。
然而,鲁迅依然没有忘掉那些看客。刻意不满足看客的观看心理,则是对这种行为、这种人的杀戮。何其难,《铸剑》玉石俱焚,而看客犹在,沉默在黑暗中的鲁迅也无可奈何。
《复仇(二)》
一个救世主,总是对这也不满意,那也要改变。动别人的奶酪,或则把人家拖离舒适区,要知道麻木久了,会怪你。当然遭遇反攻,而鲁迅也不曾退却,“悲悯他们的前途,而仇恨他们的现在”,那么如何复仇?不让这些人满意。挣扎、喊叫或者是求饶,都落入对方的圈套,于是鲁迅悲悯、他觉得痛的舒服,玩味,这种态度便是一种复仇。而他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然而,和上文一样,免不了讽刺,这对自己这种人的,自以为是救世主,得了献身的精神,要去做这种事,甘心就戮。然而人家不仅不看好你,最后杀掉你了,你才知道,你不是救世主,你是“人之子”。多么沉重的悲哀,鲁迅无法可想,他的痛苦在兹。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这是他这个阶段很常见的心境,寂寞,虚无,疲惫,不再那么勇气勃发,斗志盎然。周身都是空虚,唯有靠那希望来自欺,不至于完全垮掉。原是以为,自己的青春当然迟早会过去,但是会有新的青年,和青年一定比老年更好。今天或许不这么觉得了,那么自然就走向了虚无和寂寞。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绝望是虚妄的,因为虽然有了太多的绝望,毕竟不能穷尽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不绝望的地方(事情),鲁迅用一贯的“怀疑”态度来处理,那么好了,这个态度已经不是一开头的那种痛苦;但,希望未必就不是如此了吗?希望到底有,还是没有,有有谁知道?《记念刘和珍君》那里:“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也走向了虚无主义。因而感到的非他,仅仅是寂寞。
《雪》
“那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先生自喻也。
《风筝》
这篇文章写的直白,不像是前面那种隐晦的文风。
请求宽恕,为童年的事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可是却发现对方都忘记了,而对方的忘记并不能让鲁迅解脱,反而是“只得沉重着”,再也无法摆脱这沉重。
往另一个方面想,中国人,或者说人类,都善忘的,于是之前做的丑事恶事,一段日子过后,都不再有人记得。没有记忆,也就无法从之前的错误中获得什么反思性的力量,而人类只能继续走入历史的循环之中。
《好的故事》
好的故事没法凝视,如果要凝视,那个梦境就不复存在。人不思考,他永远在一个自得而自洽的世界中生活,而一旦有了凝视、有了思考、有了怀疑,那么一切美妙都不复存焉。
《过客》
又是戏剧的格式,少见。
客要往前走,他是极端的,永不回头,甚至不歇息。但他知道,他也只是一个过客罢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是一个过客。老翁,其实是客要反对的,他已经固化了,永远如石头一般,不再变化,也没了好奇。对世界没有好奇的人,本质上已经死了,将死之人而已。
客要讨水,这个细节很好。故事层面上,是合理可信的,而象征层面上也有意味,这便是好的小说了。讨水,那是为了给他能量,可以继续走下去,于是要谢姑娘。翁不让谢,“这是没好处的”,怎么理解?没好处是否等于有坏处?没好处,当然是说,口头的谢,没有什么作用;若是有坏处,那便是让这女孩从此看轻这执意要走的勇士了——鲁迅遭到的青年的冷遇乃至背叛,或可做此解。
客要往前走,前面是西边,是太阳落山处,是西天,是坟,是一个人的终点。坟,对客是终点,对女孩是花花草草的地方,客到坟,就不再能走动,但他关心的是:坟之后是什么?虽然没有人知道,而他只是关心着,因为那才是他要看到的,尽管他知道自己看不到,但是他也要往前走,他要让别人可能可以看到。
客的果决,憎恶,即便是人的尊敬和悲哀的眼泪,他也统统不要,他要的是那自由、善良的地方,尽管他为之付出一切,丧失生命,也在所不辞,那也比死在那个到处是牢笼、地主和悲哀的眼泪的地方,他知道,那让他获得尊敬的眼泪,也不过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眼泪罢了。因此,他宁愿用掉一切,耗掉自己,也不愿受这虚名、世人的瞻仰,他所求的,只是那脑中的更美好的世界而已,这是真的战士。
而他需要饮血,血才能恢复他的力气,水是不够的,水让他的力量更单薄。——这解释了鲁迅问什么要复仇,要嗜血。杀人者,要以血的代价偿还,不如此,则他的力量有限。
有个声音催着他走,翁原来也听到过,但终于是不理它了。客也想歇,但他一看翁就知道了,这一歇,不知道何时还能站起来,还能继续走下去,于是他不歇,这是何等勇毅!
他不要女孩的布,布施。受了女孩的布施,她就和他有了关系,按作者和许广平的话讲,他不再放心,和他有关的人,只有都死了,他才放心。而他舍不得这么年轻的人死,于是不想和他们有关连。这话该怎么理解,我还不太明白。
《死火》
于冰谷之中,找到那么一点死火,要么烧完,要么冻灭,总之是无法存留。那鲁迅要烧完,而非冻灭。他要自己死,不要别人逼迫着他死。死是生命的大欢喜,那是自由的最高体现,不能让别人扼杀他。——但他最后还是被别人扼杀了,大石车撞死了他。(多说一句,这真是鲁迅的写法,末尾一定要反转)但即便如此,那也无妨,因为掉进冰谷中的大石车,无法再找到死火,而身上曾经有火,便死而足矣。
《狗的驳诘》
甚至是不如一只狗,极端的侮辱,让他只好自己逃走。内心的苦闷无助。
《失掉的好地狱》
又是记梦。鲁迅在这个集子里常常记梦。
不太懂。
《墓碣文》
还是不太好懂,当然,有人会解读,而凭他人的理解来理解,不算本事,虽然未必就没有好处。
鲁迅是这样的人: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他也是这样的人:抉心自食,脸上不显哀乐。
——成尘之时,将见微笑。
《颓败线的颤动》
不很懂,只觉得这个女人的形象很肃穆。
《立论》
太熟悉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如果都不想,只能敷衍搪塞过去。
《死后》
不仅会死,还要论死后。这是鲁迅的特色。
死后讨厌人来论,这些人无非是些苍蝇,让人厌烦。他自以为自己的作用不在给人做研究,而是要引起人的向前看的精神。
看客依然很多。
“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个快意怎么理解?
《这样的战士》
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们而作。”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只会诉苦,相信通过诉苦,获得别人的慰安,便可以重新获得力量。鲁迅要的是血的代偿,而不是一两句口头上的慰安之语。
聪明人最善于做一些口头安慰,其实并不关人家的死活。
那种只晓得为人出力最终却遭人嫌弃和陷害的人,就是傻子。傻子好心助人,而且他知道非这样助人不可,最后却被被助之人所诬告和陷害。
而奴才呢,明明是吃了苦,却从不想是谁真的造就了他的苦,反而因得到了主子的夸奖而感到快乐,这就是奴才,真真切切的奴才。
《腊叶》
病叶救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它依然会黄掉;而且不仅是无济于事,甚至过不久也就把他给忘了。《<野草>英文版序》里面说得清楚,这是为了那些想要保存鲁迅的人而作的,枫叶因病而美,暂时被人保存,但之后也是会被忘掉的。
《淡淡的血痕中》
在鲁迅看来,造物者实在是怯懦:如果不愿意让人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有本事就让它更坏啊,它不敢,不敢让尸体长存,让人类永葆记忆,记得这些人为何而死,让人们有持续的力量。造物者没有这个勇气,因此它让人们善于、惯于遗忘。
人类中的怯懦者——所谓造物者的良民,面对悲苦不敢说什么,只能等着新的悲苦的降临。
而叛逆的勇士屹立、洞见、记得、正视、看透,这是鲁迅的期待。
《一觉》
对青年的爱,“他们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