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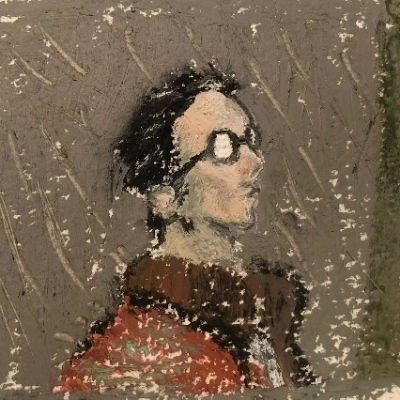
读完这本书后,笔者搜寻了解了作者的生平,才发现这本历史地理学著作的作者,首先应该被称为一名经济学家。作者颇有国际风味、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在那个年代实属罕见,堪称纵横捭阖的人生也无疑为他的天才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在开始之前,关于本书的一个基本概念笔者认为是十分有必要澄清的。本书书题中的“基本经济区”曾使笔者十分困惑,按照笔者先入为主的字面理解,这个概念描述的应该是类似于在全国范围内划分的若干经济地理单元,也就是对经济区域的地理划分,然而笔者开始读这本书后却始终无法将作者所讲与这种预设联系起来。反复揣摩后,笔者意识到自己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应该在如下的意涵中去理解。
“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未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排他性的水平。这些区域高度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没有机械工业、现代交通通信设施和先进经济组织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冀朝鼎(1935),《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岳玉庆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也就是说,本书所讨论的“基本经济区”应该被理解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率以及漕运等条件最好,使得这一地区对控制全国起到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地区。其所指的是单一的高价值区域,而非若干有着不同特征的地理区块。
为了确认自己的上述判断,笔者对照了本书的英文书名: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分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明确了其所讨论的是Key economic areas,即“关键经济区”,而非“基本经济区”。这个信息显然是被现有的这个中文版本书题省略或者部分曲解了。
本书结构严谨有序,第一章就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概念给出了定义,第二章开始分析了水利诸要素(水、土壤、泥沙)对基本经济区形成发展的影响,第三章对历朝历代水利活动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简要统计,第四章探讨了“治水”作为国家职能的历史,第五六七章则分别论述了基本经济区由北向南发展或转移的过程和趋势。在笔者看来,本书的核心就是从水利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如果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显得有些稀松平常,但笔者随即通过检索资料了解到,“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这个命题也不过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才由张家驹先生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中正式提出的,其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堪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 虞云国(2010.03):《“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最早提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0321期]。这意味着在作者写作的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南迁这一问题尚远未如今天一样成为常识。至此笔者不得不再次为冀朝鼎在写作本书时的高远目光感到赞赏。同时,冀朝鼎从水利和经济角度、张家驹由历史社会角度,分别发现并研究了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具体内容方面,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关于“中国治水的地理基础”,作者在第二章开宗明义:“以中国的地理条件而言,如果不在农业实践中坚持发展一种水利体系,农业生产就绝对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并引述魏特夫的话说,“灌溉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是集约农业的必要条件,就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就像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煤铁的基础上一样。”这些强调了水利工程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从水利角度切入中国经济分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仍然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指出了中国早期经济区的黄土的特性,即黄土其实有着良好的肥力,但是这种肥力需要在有效的灌溉之下才能发挥出来。显然,这种灌溉可以经由两种方式完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水利工程。从这种角度来说,“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水利提供了基础,而水利的发展又决定基本经济区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受到它们的制约。”
笔者认为耐人寻味的点在于,作者接着对历史上经济长期衰退的西北地区进行了考察,我们通常的认识是,西北地区在历史时期内的衰退主要是因为气候原因,但作者指出不能把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更加可靠的解释应该是统治集团更加专注于发展南方的肥沃土地,结果忽视了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如果用地理学的思维,很容易陷入地理决定论的窠巢,即认为中国的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变迁,但这一推论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在第四章,作者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观点,试图澄清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的部分历史问题。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治水者,传统上人们认为他曾经成功治理了泛滥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洪水,是尧和舜的继承人,但顾颉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顾的考证,在历史记载中,禹出现于西周时期,而舜和尧却出现在春秋末期。在尧和舜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禹了,但是在历史年表之中,顺序却与之完全相反。顾颉刚认为禹事实上是长江流域居民中间的神话人物,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而他治水的故事发生在会稽。禹的传说从会稽传到安徽的涂山,从涂山传到楚,又由楚传到中国的北方。顾颉刚认为禹的传说体现了长江流域人民对治水的迫切需求。他的这一理论无疑挑战了神秘化的治水起源理论,使得我们对中国治水起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社会前提。在古典封建时期,大型的水利工程是难以兴建的,因为缺少可用的自由劳动力。只有从战国时期开始,随着生产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生产力提高,井田制逐渐瓦解,私人土地所有制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劳役和兴修水利工程才成为可能。
总的来说,作者在书中的论述是相当充分全面的,第一次使用专业化、学科化的表述,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影响基本经济区的各种因素,将这一创新的概念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观点放在将近九十年后的今天也并不显得过时,仍能给人启发和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