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社會性的不可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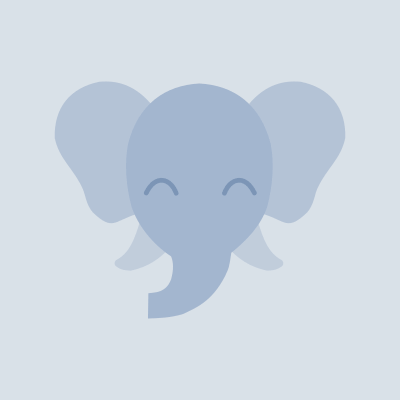
金基德的電影,總於苦澀中滲透著一股淡淡的甜味,更多的,是對人性與社會性的不可對話的無可奈何。
《呼吸》是第一套我看他的作品。女主角面對丈夫的外遇,心中的鬱結無從可訴,於是找上了男死囚,與他分享她自身對愛情、對死亡的記憶。二人漸生的愛情沒被社會接受,女主角的丈夫沒有理解過二人之間的愛情,只視之為妻子報復的出軌行為;《聖殤》如是,專為高利貸收數的男主角看似冷漠無情,對欠債的人絕不手軟,一個以金錢為上的社會,情變得多餘。沒人想了解男主角冷漠無情的表面底下蘊藏了那麼一顆渴望親情的心,也沒有人關心種種所謂不合乎人性的報復行為;《空房間》之中人性與社會性的不可對話更是明顯。男主角潛入各個空房子之中,雖說是非法入侵,可是他卻幫屋主打理房間、修理電器、解救被虐打的女主角、安葬倒斃在家中的弧獨老人。這些充滿人性的行為沒有為他帶來救贖,他被拘捕、被收監、被鞭打、被警察出賣,在現實的社會面前,他帶有人性的行為顯得不值一顧。
《空房間》已差不多是十多年前的作品,可電影故事的橋段還是新穎得教人震驚。一個不斷潛入空房子暫居的少年,遇上了被虐的婦人。兩人展開了一同潛居的生活,他們都是流浪者,在社會中漂流浮沉,但他們心有所居,因為有了對方,那裡都成了他們的家。
金基德的電影亦總是處於虛幻與現實之間–就如片尾旁白: 「這個世界,有時候分不清是夢幻還是現實」。片尾的一段確實令人動容,男主角亦真亦假地生活在女主角的家,與女主角和她的丈夫三人同一屋簷下。幾乎全戲都沒有對白的女主角,用口形跟男主角說了一句「我愛你」,始才發現,兩人之間即使在戲中全無對話,情卻早以在空氣間互相流轉。女主角的丈夫見不到男主角,男主角彷彿只活在女主角的眼中。
其實由始至終,也只有她的眼中看到過真正的他。
PS: 「人性與社會性的不可對話」此詞原自葛亮寫《空房間》的影評,收錄於《繪色》之中,有趣的是,葛亮提到了 “3-iron” ,原來指高爾夫球的三號球杆。導演曾就此解說:「很多人買了三號球杆,卻只放在球袋裡蒙塵﹔很多人有家,卻只把家人留在家裡,這與空房子有什麼分別?」相對而言,港譯的《感官樂園》就變得十分嘩眾取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