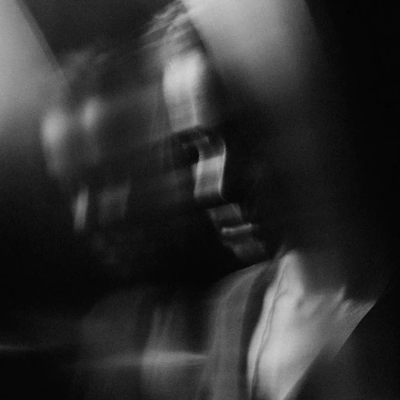众缄之罪:中国人的宗教
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知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
以上三段文字摘自张爱玲作品《中国人的宗教》,在此略作延展。
文章之中,张爱玲对中国人的宗教从上等人与下等人两个方面剥离开进行了阐释。我不得不想说两句与文题无关的话,如今大多数人,尤其是做文艺的人,常常强调众生平等,但心里或多或少藏着媚上欺下的心思,诚然,社会的上等人与下等人乃至边缘人,生活与思想本是不同的,且并不单以资产多少呈现出渐变的姿态。与人性有关的事常常是复杂的,所以不作赘述。张爱玲是以民国时期的天才诞生的,她天生自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如此直截了当地将自己与所有的世人剥离开,并分为三六九等,对她是自然的,也更适合宗教这一话题的客观阐述。
回到文题,张爱玲生在民国,到现在已近百年,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形式,却似乎没有改变。追溯千年前的祖先,到而今的我们,从历史记载和社会风气看,宗教对于我们中国人从未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或意义。这样说或许过于绝对,但宗教至多只在一定范围内对我们进行了行为的约束,但没有过对思想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的君主,百家学说中的儒家,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宗教经得起随便多少亵渎,从温陵居士李贽等的反正统思想可见一斑。一如张爱玲写道,王母与麻姑都不是信仰的印象,但中国人并不反对他们与观音大士平起平坐。
但我将这个话题提出来,并不是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文艺者的身份,为我们现今的文化盲点感到悲哀,所以我给此文题名“众缄之罪”。众缄,意而今我们信仰上的空白,“这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我定义为罪,是因为这种空白,不管在多久以前还是现在,都可以说是我们罪恶的根源。如果我们信佛而一心向善,哪怕作为一种不可能的假设,我们也大概可以想象到一些大同的色彩来。
这并不等同于对宗教的盲目推崇,只是希望我们能有所信仰,凡事对自己有所思索,凡事抱有敬畏之心。
在世界的角落,那些贫瘠的偏远的地方,有身着宽大藏袍的苦行者,怀抱着圣洁虔诚的心思,在艳阳天的古道上,三跪九叩。路途的险远在他们面前竟显得一文不值,只能作证他们内心的苦修。但我想,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何为苦修,他们只是走在通向信仰的路上,所以那些俗事都成了无足轻重,一如那落了一地的烟尘。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给了佛祖,纵然身周已经如此艰难,也只在寻求那些在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无用之物。但我们所追求的时间和价值,在他们看来,怕也不过是废铜烂铁。幸而多人有所觉悟,大肆呼吁着解救文化,精神远比物质来得更为重要。这句话本身没错,但那些人常常将信奉神佛和追求精神等同了起来,这却是我所不认同的地方了。在我看来,那些宗教徒与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看到的世界不同,是从文化衍生的价值观差异,并没有谁对谁错。若是要我们皈依佛门、一心向道,这既是痴心妄想,也是对宗教的亵渎。
所以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所提倡的不是宗教,而是信仰。
我认为,宗教只是一种狭义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四字即可概之——有所敬畏。因为有所敬畏,所以凡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会向善。
那些信徒,有的一生都在朝圣的路上,他们的内心纯净,必然有所敬畏,且深信不疑。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宗教的人就是恶徒。一个人可以不信奉宗教,但必须有所信仰,而这也是精神追求的一种体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追名逐利的人,既被人羡慕,也被人讥讽。其实,看重名利又何妨呢?只要心中有善念,依旧能敬畏生命,依旧有为人的底线,不也已经足够了吗?这样看来,最基本的信仰我们还是触手可及,看到弱者依然会心怀悲悯;追逐名利也不会不择手段,从未放弃自己的人格。纵然信仰的力量远不及于此,但已达到“有所敬畏”的境界,以人格为信仰。
然而,那些无所信仰的人,依旧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说着粗劣的话,做着冷漠的事,他们常常穷凶极恶,无所不至。比如鲁迅先生笔下围观同胞被屠戮的麻木不仁的国人,或者那面无表情路过被碾压儿童的路人。他们失去了真诚和善念,他们无所信仰。不必说他们没有宽悯情怀,他们甚至早已经丧失了人性,放火行凶,不辨善恶,当他们中的一部分进了牢狱,或宣判死刑时,他们依旧坚定地以为自己没有错。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是非最基本的判断,荒谬而不可理喻。这无疑是无所信仰最惨烈的表现形式了。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这说的是葛藤、荆木相互依存,蔹草、野土有所依托。我想,以此来说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怕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生而为人,有所信仰,是我们在精神之路上追寻的真正价值,我们依信仰而生,而信仰,也因此有了超越死亡的意义,人道才得以相承。只有百年之后我们拥有国民信仰,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古国,方能生生不息地传承绵延。
愿信仰与人道在时代的长河里厮磨,成全各自的修行,并最终趋于唯一存在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