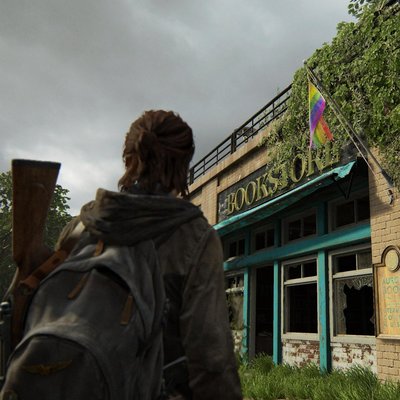《一些笔记》
主要还是摘录前几篇文章:
《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述之后才成为“历史”。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历史复杂巨大有多种可能性,但是绝大多数都被简化,只留下符合意义和目的内容。历史是“有中生有”,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历史来,其他的历史被归为野史神话。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不加怀疑与批判,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因此作者认为历史学家有三种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是切题的一篇文章,作者主要讲了身为历史学家,他的使命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反抗,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毕竟有很多历史的叙述经不起深入推敲。同时作者还谈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责任,举例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正是来源于德奥历史学家的民族史讲述。中国的民族主义,点到即止。“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作者先从中国现代历史学建立时提出的观点“史学就是史料学”开始讲起,首先肯定了正确使用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正确性,批判了崇古信古不辨真伪使用史料的“古董学家”,然而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传统史料学强调史料真实可靠,然而作者更为认同孙正军的“史料为什么呈现这个样子”,同时还认为,除了存在的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都可以作为历史来研究外,“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举例著名油画作品《井冈山会师》《开国大典》抹掉的人物,也要作为历史来研究。因为这涉及到了“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在造成主动的遗忘和强制性的遗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意义的。“历史是被说出来的”,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改写遗忘的就越多。
《遗忘的竞争》
本文重点关注了遗忘。遗忘制造历史。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有文字时代里,参与竞争的某些历史论述虽然被压制排挤,但仍可能通过书写载体而幸存,或残留一点残迹,等待未来的同气相求者的发现再次登场。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以及如何实现何事的遗忘,我们就不能离历史更近一些。第二部分详细讲述了崔浩的国史之狱,却以此为例,讲述了遗忘在文化转型中的积极意义。书写帮助权力集团建立稳定的有利的唯一的历史叙述,当已有的历史叙述成为包袱时,史案和文字狱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作者从一次走越南的“汉喃研究院”而引出了古代多语言社会书写语言与日常口头语言的分离,汉语社会对非汉语社会的渗透与影响。可以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到古代东亚历史的变迁。历史显示,深度接触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均匀,上层语言(书写语言或官方语言)对下层语言(非书写语言或被统治阶层的语言)的渗透,通常是更深更快更有力的。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19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本国内往往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世上本无黄种人》
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 reticulate evolution ),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 socio-cultural construct )。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事实上,我们听到的《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唱歌人却用“遥远”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
《双螺旋的低语》
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一定是越往上越多的,但是家族的族谱却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向下无限开放的金字塔。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家族并不是一个和村村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种族之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