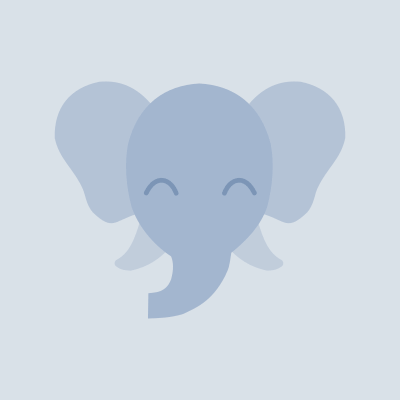未完的对话
一位青年与哲人的对话记录成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并且成为了畅销书,获得很多好评。在众多读者中,有另一位青年,他读完这本书感觉受到很多启发,但也有一些还不太满意、没有完全解除疑惑的地方。幸运的是,这位青年读者因为朋友的关系来到了哲人的小屋,得以与哲人面谈,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酣畅淋漓地讨论一番。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青年迫不及待,开门见山地与哲人讨论起来。
宝贵的启发
青年:先生,您知道,我是《被讨厌的勇气》的读者。读这本书让我受到了很多启发,有很多收获,也促使我进一步去思考。
哲人:真的吗?
青年:真的。例如您提出的“课题分离”原则,其实正好与我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谋而合。我没有您这么高的理论水平,没法总结出这个概念。但是在我当年逐渐走出青春期的时候,上高中时又开始过集体生活,我也逐渐体会到,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应该就是不要对别人的选择强加干涉、要与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自己的付出不要期望一定得到回报。当我上大学期间看了一些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书和文章,就更加明确要把尊重别人的自由空间确立为我的信条之一。现在看了您书里讲的道理,我感觉我个人的信条得到了印证,我也会更有信心、更坚定地践行课题分离的原则。
哲人:能对你有帮助,真是太好了。
青年:是的。还有,您提到要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页122),要想到自己属于更大的共同体,全世界、生物与非生物、过去与未来都是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这一点太有启发性了。也许,这正是当今世界消除与身份(国家、民族、宗教、文明等等)相关的各种纷争的不二法门呢。
哲人:的确,我思考这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你关心的那些问题,我想阿德勒当年应该也想到了。
青年:您还提到,要多与别人建立横向关系(按我理解就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纵向关系,要对别人表示感谢、鼓励而不是评价(页131)。这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方法。我在工作场合已经用到了与同事的相处中,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真的要感谢您呢。
哲人:哪里。我的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我才是最高兴的。
青年:但是,先生,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味对您和您的书称颂有加,那倒反而对您不尊重了。您是哲学家,我听说,在学术界对一个学者表示尊敬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向他提出批评,与他展开辩论了。是这样的吧?
哲人:确实是这样的。你批评一位学者,往往表明他的观点很重要。你也是学术圈中人吗?
青年:不是,我不是做学术工作的,但我关心思想文化,所以也对学术界的惯例有所了解。
哲人:是这样啊。业余爱好思想文化,还真是难能可贵呢。
青年:您过奖了。那我就开始我的批评了,您不要介意我班门弄斧(笑)。
哲人:哪里哪里,请开始吧,我迫不及待地想听你的意见了。
一切都是主观的吗?
青年:首先,在书的引言里,您提到一个关于井水的例子(页XIX),您说井水的温度是恒定的,但不同季节我对井水温度的感觉却不一样,所以您说“如何看待”这一主观的观点就是全部。但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好呢。
哲人:为什么?
青年: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您自己也说了“夏天喝到的井水感觉凉爽,而冬天饮用时就感觉温润”。这其实是一个规律。我对井水温度的感觉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的,也就是被这个客观规律限制。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转变我的主观看法,在炎热的夏天都不可能感觉井水很温暖。可见,并不是只有我的主观才有用,规律也在起作用啊。
哲人:嗯,你说的有些道理。但这也只是一个例子不太恰当吧。
青年:但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观感受总是被客观因素制约的。
哲人:但是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我认为主观感受是可以摆脱客观制约的。你感觉泉水是暖的,可能只是因为你心里很暖。
青年:后面也许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我想讨论下一个例子,您指出,假如某个人过去曾遇到过父母离婚的变故,那么影响他的其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何诠释”(页14)。
哲人:确实如此。
青年:这个观点,我在一般意义上是同意的。我也认为人不能把自己的缺陷完全归咎于过去的原因,不能用决定论为自己开脱。但问题是,“如何诠释”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由自己选择吗?如何诠释是否又决定于其他因素?我听说诠释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哲学上有很多理论。我不太了解理论,只能非常宽泛地讲,恐怕“如何诠释”必然会受到当时当地的传统、共识、道德准则的制约。这就像刚才说的,对井水温度的感知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一样。假设我生活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我的同胞们认为离婚是极端可耻的事,父母离婚后孩子也成了“孽种”。自从父母离婚起,我身边的人、学校、媒体都在不断对我强化这个观念。那么我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和不断的灌输之下,还怎么能发展出不一样的诠释,摆脱父母离婚的阴影呢?
哲人:可是阿德勒的哲学就是教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只专注于选择你自己对事实良性的诠释。
青年:可是正如您说过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特别是,政治哲学有个社群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群中的存在,人的认识完全是由社群的传统、共识决定的。假如这个学派的理论有一点道理的话,那恐怕让人们摆脱社会共识、选择另一种诠释就是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哲人:你说的有道理,哲学上是有这种看法。但以我的观点,我仍然觉得人不可能完全被传统决定,人是可以选择自己对事实的诠释方法的。
青年:嗯……这个问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了,我无力再分析,它实在太复杂。
不幸真是自己选择的吗?
青年:您还提到一个例子,说无论什么样的犯罪者都不是纯粹想要作恶,而是为了某种“相应理由”,达到一种利己意义上的“善”(页21)。我觉得这又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呢。
哲人:我是举过这个例子,为什么不恰当呢?
青年:先生,我也同意,除了某些特殊人群,比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犯罪者作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主动选择的。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也认为是这样,所以对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就要接受法律惩罚。假如一个人的行为别无选择,那也就不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您由此推出,不幸也是自己选择的,又没有给出其他论证。这不是一个能够成立的推理啊。作恶和不幸是两件事,虽然相似,但前者有选择并不会必然推出后者也有选择。
哲人:虽然不能形成一个严格的推理,但我认为能形成一个合理的推断,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
青年:那么我就觉得,“不幸也是自己选择的”这个观点缺乏可靠的论证了。后面您又进一步说,人们会把不幸当作武器,利用弱势者的特权地位。比如婴儿就总是用弱势地位来支配大人(页49)。
哲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吧。
青年:以当代人的育儿方式来说,弱势的婴儿确实支配着强势的大人。但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人的责任感。推而广之,您说不幸的人拿不幸当武器,恐怕,他实际上利用的不是不幸本身,而是别人的道德感、同情心,由此形成迫使别人照顾他的压力。一旦别人的道德感、同情心没有了,那么他也就无法“利用不幸”了。比如,您说弱势的婴儿支配大人,但其实也有大人利用自己的强势来支配孩子,特别是在传统的育儿方式下就更常见了。这就是当强势者的道德感、同情心发生变化的时候产生的情况啊。
哲人:但是,利用自己的不幸与利用别人的道德感、同情心又有什么差别呢?
青年: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在于,如果认为不幸的人是故意“制造了”不幸并拿它当武器,那我们是否还需要同情他人的不幸呢?难道同情他人的不幸不是一个重要的美德吗?
哲人:啊,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找机会专门论述了。
青年:好的,有机会我再找您讨论。先生,您还提到人的性格和秉性其实是生活方式,也包含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并不是不能改变的(页22)。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某些人说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坏脾气所以难以与别人相处,或者主张要不管别人的感受、任性地“做自己”。您很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有害的观点。但是,您说只要有勇气就可以改变自己,我觉得却又是不真实的。
哲人:为什么呢?
青年:有一种情况,我不能改变自己,恰恰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世界观,改变以后我的世界观就无法自洽。比如,因为我无法接受人与人的不平等,所以我在遭遇别人用不公正或损害尊严的方式对待我时,就不能忍受,感觉很痛苦。但我无法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现实,因为调整到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是跟我整体的世界观矛盾的。那怎么办呢?
哲人:人人平等确实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当然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但假如你要求的平等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伤害其他值得追求的价值,那么你确实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行动。是别人,或者环境需要改变。你不用改变行动,但仍然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用更自信的态度去对抗不平等。
青年:那么,我遇到的不幸就不是自己选择的了(笑)。
哲人:客观上的不幸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否沉浸在不幸的心态中还是可以自己选择。
青年:那么就又回到刚才的问题,是否一切都是主观的了……
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吗?
青年:先生,您说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人是因为太惧怕人际关系所以才讨厌自己(页37)。我同意人的很多烦恼来自人际关系。但是难道就没有因为自身不完美而带来的烦恼吗?后面您自己又说过,健全的自卑感不是来自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自与“完美的自己”的比较(页51)。难道这种“健全的自卑感”不也会带来一些烦恼吗?
哲人:可是,如果只有这种健全的自卑感,它带来的烦恼没法跟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相提并论。甚至有可能,它带来的是追求理想的快乐。
青年:可毕竟,人生是有限的,追求理想纵然快乐,但时间的压力、自身能力的不足也会带来焦虑。
哲人:所以我们也说了要重视当下,不要去管过去和未来。当下的每一点成果和进步,甚至只是追求的过程,都能给你快乐。
青年:好的,活在当下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可能还会提到。
人一定能从竞争中脱身吗?
青年:现在我想先请教一下关于竞争的问题。您告诉我们,要从竞争的怪圈中解放出来,没必要战胜任何人,就能体会到“人人都是我的伙伴”了(页56)。但问题是,如果我处在一个资源稀缺,必须为之激烈争夺的环境中呢,难道还能够从竞争中脱身吗?假如我的成败仅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成败,那我也许还能不在乎竞争的结果。但如果我肩负着一个团体的责任,那怎么能轻易退出竞争呢?
哲人:可是你应该想一想,你真的需要争夺那些所谓的资源吗?重要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你如何看待环境。
青年:好吧。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始终是不相信一切环境条件都可以由主观来改变的。尤其是涉及到共同体传统、共识的时候。下面我要继续请教一种特殊的竞争,就是言语之争。我的前辈(指《被讨厌的勇气》里与哲人讨论的青年)向您请教了发怒的问题,他问:“即使对方明显找碴儿挑衅,恶意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也不能发怒吗?”(页61)您回答说没必要依赖发怒这一工具,语言才是更好的工具。我很同意这一点,我也很讨厌在沟通中动辄就发怒的人。我甚至连说话语气趾高气扬、不容分辩的人都很讨厌。
哲人:难得你有时也同意我的观点啊(笑)。
青年:不不,其实您很多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只是我今天要珍惜机会,多向您请教我有不同意见的观点。
哲人:我明白的,刚才是开个玩笑。
青年:但我又觉得,有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使用发怒来作为一种信号。
哲人:什么情况下呢?
青年:语言和逻辑失效,或者来不及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我和您在这一点上有分歧,根源在于我对语言的力量不如您那么有信心。语言失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比如最近这些年,由于社交网络的流行,我们看到争论或辩论无处不在,但很多时候有理有据的一方并不能占上风。甚至在相当清晰明了的科学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是否相信新冠疫苗的问题,很多人宁愿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当然,这种情况下,愤怒也没什么用了,我们只能退出争辩,等待长时段的教育或者观念市场竞争的结果,看看是否能带来好的变化。第二种情况是,我遇到的对手习惯于拿气势或者权势压人(就是我刚才说过特别讨厌的那种人),他不能接受正常的逻辑,永远都不会承认事实和逻辑推演的结果,永远都会用诡辩的方式逃避智识和道德的责任。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也可以退出竞争,但是如果我有紧急的、无法绕过的事情需要对方配合呢?如果已经试过好好说话的方式而不起作用,我想只能用愤怒作为信号,让对方知道我不会退让,也许还有希望达到目的。否则还有什么办法?
哲人: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很可能无法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双方都避免发怒,用语言和逻辑来沟通。
青年:但这是双方的事,并不单单取决于我啊。基督教《圣经》里面有巴别塔的故事,讲的是人们的语言发生了混乱,互相无法理解。我想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表明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无法靠语言沟通,已经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当代人面对更加复杂的世界,更是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了。
哲人:你说的没错,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靠语言获得共识。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更多地依靠语言和逻辑的力量。发怒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青年: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环境对人没有影响吗?
青年:那么,下面我就想要请教“人生谎言”的问题了。您说,通过归咎于他人来回避人生课题,其实是人生的谎言,我们的生活方式只由我们自己决定,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缺乏勇气(页71)。我非常同意,通过归咎于他人或环境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是懦弱的。
哲人:你这么说,一定还有不同意的地方了?(笑)
青年:是的,被您发现了。我不同意的是,我的生活方式恐怕不是只由我自己决定的。而且,只把责任归咎于自己也不见得是有勇气的表现。事实上,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所有问题都是个人努力不够,不用从社会整体层面来解决。但实际上,很多问题只能从社会整体层面才能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说“个人努力不够”是非常容易的,看到并指出“房间里的大象”、推动社会变革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
哲人:我明白,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不要推脱个人的责任。
青年:正如刚才所说,我对个人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完全同意。只是,我认为清醒地认识到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也是一种勇气呢。
可以不管别人的期待吗?
青年:下面我想请教一下要不要满足别人期待的问题了。您说:我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们没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页81)。
哲人:是的。
青年:上面这句话包括两半句,您是连着说的。但是,其实这两半句话有不同的含义。“我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没错,我也并不认为别人的认可是我的人生目的。甚至可以说,我也不像尼采一样认为荣誉是我的人生目的。但是,“我们没必要满足别人的期待”是另一回事,这半句话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如果我只有获得别人的认可才能取得某种重要的资源呢?如果我只有获得别人的认可才能在重要的事情上赢得别人的合作呢?这样我就当然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了。而且在现代社会,由于大部分事情都必须依靠合作才能完成,所以需要靠别人的认可来赢得合作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哲人:但是,你不需要刻意满足别人的期待。你只需要让自己更完美,更能胜任你的工作,自然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可,从而赢得你需要的资源或合作。这也是我说过的“健康的自卑感”所要达到的目标。
青年: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我正好也有疑惑。您也说过,关于自己的人生我们能够做的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别人如何评价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无法左右(页89)。
哲人:是的,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不用满足别人的期待。
青年:但是,如何知道我所选择的真是最好的道路呢?
哲人: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有理性,通过学习,可以学会选择最好的道路。
青年:可是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对很多人来说,无法与自己所处的社群环境割裂开来,他们从小是从社群的传统、共识中来学习,并且通过社群的期待或评价来不断校正自己的道路。这样,“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和满足别人的期待,其实是融为一体的。
哲人:我知道,你说的是你之前提过的社群主义的观点。但我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
青年: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其实我也并不是社群主义的信奉者。我还想讨论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也是让我觉得无所适从的一个具体事例。您提出,假设有一个毫不讲理的上司一遇到事情就大发雷霆,无论怎么努力他都不给予认可,甚至都不会好好听我说话。您说,我没有必要主动迎合那位上司,因为那位上司而干不好工作是“人生的谎言”(页90)。
哲人:是的,这也是课题分离的一个应用。
青年:可是对大部分工作来说,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有跟上司处好关系,我才能得到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自由去做好我的工作。所以管理学中还有所谓“向上管理”。我不可能把干好工作和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分开的。
哲人:对,的确不可能把上司和工作完全分开。但我说的是,迎合那位上司不是必须的。你至少还可以离开他,换另一份工作啊。
青年:嗯,理论上是这样。但现在新冠疫情还很严重,经济不景气,很难去换一份新的工作啊。(笑)
是否要关注别人的课题?
青年:先生,您还提到了您和您父亲的往事。您父亲曾经殴打过您,导致你们父子关系不好。但是您首先改变了自己、靠近父亲,最终也导致父亲发生了变化,父子关系得以修复(页103)。先生,说实话,我好羡慕您和您父亲。但我觉得,可能不是世上所有的父子都可以这么幸运。
哲人:为什么呢?
青年:因为我知道,世界上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父亲,即使儿子改变自己并主动靠近他,父亲还是会继续殴打儿子,继续用粗暴的语言和态度对待儿子。在其他关系中,比如夫妻关系也会有这样的例子。那又该怎么办呢?
哲人:相信我,你跟大多数人的关系中,你的良性变化也会带来对方的良性变化。但如果对方没有变化,也没关系,因为这是对方的课题。你至少可以不在乎他的态度,或者离开他,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青年:如果离开他,那就不是关系修复了啊。
哲人:从你单方面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是修复了。
青年:好吧,好像又回到是否一切都是主观的问题了……先生,您的观点还有一点是我非常怀疑的。您说要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使遭遇背叛也要继续相信,这样对方也很难屡次背信弃义了(页149)。
哲人:是的,我相信是这样。
青年:但是,关于博弈论的研究结论不是这样的。根据研究,更好的策略应该是:我默认相信别人,但是当发现对方背叛了我一次,或者我观察到他背叛了别人,我就不再相信他。对每一个他人都应该如此对待。(见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合作的进化》)
哲人:但是,这样你就必须不断观察别人是否背叛,就可能又生活在怀疑之中了。
青年:但是,毕竟我遭遇的背叛,有可能是致命的啊。我遭受的背叛越多,致命的概率就越大。
哲人:致命的背叛,这种情况太极端了。
青年:先生,我觉得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两个例子揭示了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别人的课题会对我有强烈的、实质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心理的影响)。比如,父亲如何对待我,关系到我是否遭受殴打、辱骂。他人是否背叛我,可能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这样,我就不能只是关注我自己的课题,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还需要关注别人的课题(不过仍然可以避免干涉别人的课题),根据别人如何处理他的课题而进行不同的应对。这是我提出的意见,不知道是否能对您课题分离的理论形成一点优化。
哲人:你讲得有道理,我会仔细考虑一下,看看是否能纳入我的理论体系中。
贡献感是什么?
青年:下面我想请教一下“贡献感”的问题了。因为我觉得,贡献感是对您的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认为人的幸福感就来自于贡献感。您说是否真正做出了贡献是无法了解的,只要产生了“我对他人有用”的主观感觉就可以了(页162)。但是您说的贡献感真的有意义吗?一方面您说不必满足他人的期待,另一方面又说需要“我对他人有用”的主观感觉。如果我对他人的期待不屑一顾,那我如何能得到对他人有用的感觉呢?如果他人不断对我表达失望,我又如何确认我对他人是有用的呢?
哲人:所以我也提出,你的价值、你的贡献感不应该是基于行动的,而应该是基于存在的。你的存在本身对他人就是有价值、有贡献的。所以人人都应该是幸福的。。
青年:人人都因存在本身而幸福?好吧。您听说过吗?有一位胡老师说过一个著名的句式,我引用一下:人人幸福,就等于人人都不幸福。(大笑)
哲人:……
当下与未来无关?
青年:先生,现在我想请教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您强调说要关注当下,我是同意的。但是您进一步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根本不存在过去与未来,过去与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关系,未来也不是此时此刻要考虑的问题(页176)。先生,过去与未来都与现在无关,那么事件与事件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您是想取消自然界的因果律吗?揭示因果关系不就是科学的基础吗?
哲人:不,我只是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我们不必去考虑自然界。
青年:可是,人生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如果人生与自然界普遍的时空性质、逻辑结构不一致,那我们如何对世界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呢?而且,我觉得,否定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的关系,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历史责任再也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此刻做的事与未来无关,那么我们当然就用不着为未来负责了。
哲人:做好当下的事,不要过多考虑未来,结果不正是对未来负责吗?
青年:可是,如果不思考过去和未来,怎样校正当下行动的方向呢?这样,就出现了您后面举的一个例子所表现出的问题。您说,假如遭受到了重大天灾,按照原因论的角度去回顾过去以及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又有多大意义呢(页179)?但是,“以史为鉴”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无法追究天灾的成因,但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的社会对天灾的应对。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人们极大地提高了应对天灾和意外事故的能力。比如,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有无数的流行病学家、社会科学家去研究我们的应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如何去改进。如果不做这些研究,不做检讨,下一次面对大流行病,我们还是无法减轻损失。
哲人: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这已经不是关于人生的问题。我会想想怎么样给你一个回答。
夜深了
青年:(看看窗外)先生,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我们已经谈论了好久。
哲人:(笑)你觉得愉快吗?
青年:当然,很愉快。我提了很多问题,有的已经得到回答,有的还没得到答案,但在我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做了更深的思考,也已经有了一些收获。谢谢先生。
哲人:我也很愉快。你的问题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虽然有些问题我还没想好怎样回答,但我会继续思考,也许在我下一本书里就会给你回应。谢谢你。
注:文中出现的页码,均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第70次印刷的页码。
作者的话:我很高兴能写一篇对话体的评论,但能力有限,基本只能提出疑问,无法展开充分的讨论。如果有人能以哲人的身份反驳或者回答我,那就太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