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文字,能拯救把它說出來的人嗎?-- 張潔平(媒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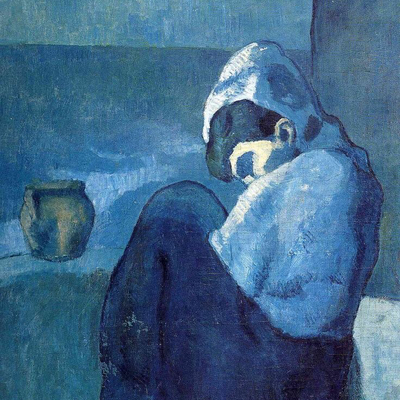
11月,我在臉書上偶爾看到衛城出版的副總編輯洪仕翰貼出一段書稿。沒有前情提要,不知道作者是誰,我只是讀了幾行,就好像完全代入了寫作者的處境,進入了那個世界:
「本書講述我對國家的愛,這份愛如何改變我,以及這份愛在我生命中出現了什麼轉變。」
「愛使人充滿希望……但危險也在於,正是這份希望使我們盲目,給予我們近乎生物本能的樂觀情緒。不知怎麼地,你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我自己就是這樣覺得。然後,俄羅斯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
「我是否知道普丁在位時間太長,是否知道他正在改變憲法及踐踏人權,是否知道我們的國家正在走向法西斯?是,我都知道。那我為此做了些什麼嗎?我用報導來敘述法西斯主義如何在我的國家裡生根茁壯,而且我寫得非常好(笑)。但光是這些並不足夠。」
那種代入感與其說是代入,不如說,我彷彿讀到了自己的世界。
我搜索作者的名字,看到了這本書的背景。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出生於1987年的俄羅斯記者,女同志,17歲開始就為《新報》工作,從實習生做到調查記者,工作了17年。直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半年之後,《新報》整個被普丁政府吊銷執照,被迫關閉。35歲的伊蓮娜流亡海外。
我從來沒去過俄羅斯,但閱讀這本書的大部分時候,就像在讀自己的平行人生。
伊蓮娜寫自己在俄羅斯長大的故事:外婆家所在的北境村莊,愛看電視新聞的媽媽,自殺離世的弟弟,自己15歲搬去生活的,那個充滿驚奇的莫斯科。她17歲開始做記者之後,去了更多地方,看到了莫斯科之外的俄羅斯,電視新聞之外的國家,遇到很多以前不會打交道的人,見識了從未想像過的人生。她也把《新報》當作一個 chosen family,和夥伴們十幾年如一日地奮戰著。
為了什麼奮戰呢?為自己親眼所見的真實,也被其他人看到。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享著「豐美而多彩」的田野,共享著戰爭與轉型帶來的哀愁,共享著千里凍原上有關死亡的神話,也共享著夏季的快樂詩歌。但是人們生活在其中的,並不是同一個世界,也不知曉、或視而不見彼此世界的存在。
伊蓮娜寫自己小時候,家裡有一台電視機,裡面「模糊的畫面播放著讓人一頭霧水的內容。有人在大叫,到處跑來跑去,都是一模一樣的播報者和聲調」,媽媽沉默地看著,她則不明白。「我很討厭新聞,也不懂為什麼有人會想看新聞。」
少年時,她偶然看到了一篇署名「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的文章,文章寫了在車臣的軍人殺害平民的事。讀完後她去公共圖書館,調閱館藏的《新報》,找到記者安娜的所有文章,逐一閱讀。
「我覺得自己好像燒了起來……原來我對自己的國家一無所知。電視騙了我。」
「我帶著這樣的認識晃蕩了幾個星期。閱讀,到公園踱步,然後再多讀一些。我想找個大人談談這件事,但是身邊沒有這樣的人──他們都相信電視。」
伊蓮娜寫:「我對《新報》感到憤怒,因它從我身邊奪走了大家普遍相信的真實。以前我從未有過只有自己知道的真實。我才14歲,我心想,卻像個無能為力的病人。」
憤怒的伊蓮娜做的選擇是:一定要去《新報》工作。3年後,她實現了目標。
作為《新報》記者的她的確見到了更多真實:
莫斯科之外,時速250公里高速列車的沿線,遼闊的城鎮、村莊、凍原裡,那些被棄如敝履的人和生活。被切斷了傳統、改變了語言、幾近消亡的少數民族聚落。像集中營一樣管理的精神病院。從冰川和凍原開始,汙染了整個海洋的嚴重人為事故……
還有失控的暴力災難:一所小學被恐怖分子佔領,1,128名人質被控制,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放棄談判而用重武器強行攻擊,造成300多人死亡,死者中有近200名孩童。災難之後,洗太平地,政府主導了長達十數年的宣傳與記憶竄改。
還有戰爭,從車臣、喬治亞、克里米亞到頓巴斯、烏克蘭,這個國家從沒有中斷過、卻總是拒絕承認的戰爭。
當我說,讀這些文本與經歷,好像在讀自己的平行人生時,我不否認,在伊蓮娜的筆下真的彷彿讀到了太多我自己做記者時親歷過、熟悉的情境與故事──
在中國,同樣被放任消亡的少數民族聚落,同樣在繁榮大城市之外被拋棄的村莊與生活,同樣可怕的人為的重金屬污染……還有貝斯蘭。那座被愚蠢攻擊犧牲掉的小學和裡面的孩子……讓我不斷地想起燒死近300孩童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想起四川地震裡埋葬了4,000多孩童的豆腐渣校舍,因為上游洩洪而被淹沒的黑龍江沙蘭鎮小學和裡頭的200多孩子。民謠歌手周雲蓬寫過一首歌叫《中國孩子》。那旋律甚至在我翻過伊蓮娜的書頁時,會自動在腦中播放,甚至歌詞還會自動變奏:「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不要做俄羅斯人的孩子。不要做貝斯蘭的孩子。」
這種共振,在外人看來是可以想像的。俄羅斯和中國嘛,哥倆好,類似的管治,類似的人禍,類似的腐敗者升官發財、普通人命如螻蟻。只是當苦難在媒體上幾乎成了這類陳詞濫調,當統治者惹人厭惡,被統治者也少有人同情的時候,一切罪惡都被奇觀化了。我看書的時候常常在想,伊蓮娜寫下的這些,我自己、和我熟悉的記者朋友寫下的這些故事,是不是永遠都逃不脫宿命:身在其中的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嘲諷、不相信;而不在其中,身在正常世界的人們,則是嗑著花生圍觀瘋人院的心情。
我要感謝伊蓮娜沒有在想這些,沒有像我說的這樣,滑向這虛無與犬儒的陷阱。我在她的書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獲得力量。那力量的來源並不是她對苦難的書寫,更重要的是,她敏感、清晰、細膩、強烈而又優美地寫下,這些經歷對她作為一個人的雕刻,誠實的每一筆刻畫。
這是閱讀本書時,我獲得另一重「平行人生」的體驗。
我也正在試著寫下自己作為記者所見證過的時代起落。每每我陷入上面所說的「宿命感」時,就難免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而每一次可以找到突破點,寫下新的500字、1,000字,都是因為,我終於嘗試著剝開「記者」這層隱身衣背後的自己。我嘗試去回憶,每一次對苦難的見證裡,那個隱身的「記者」到底遭遇了什麼,改變了什麼,隱瞞了什麼。
因此,我特別共鳴於伊蓮娜寫自己在去往危險目的地的夜路上如何被男性司機刁難,也共鳴於她如何跟只相信電視新聞的母親無法交談,共鳴於她的愛情在一個不容許這樣愛情存在的國家裡如何凋零,也共鳴於她強烈的憤怒,那沒有辦法讓死人復生、沒有辦法讓冤屈得償的憤怒,和將這憤怒轉化為無窮無盡的工作的過程。我更深深共鳴於她的愛。
就像這本書的俄語名字所寫的「我深愛的國家」。伊蓮娜筆下的土地,土地上的傳說,那麼哀愁,那麼美。即使有那麼多罪惡,她袒露身體和靈魂去體驗罪惡,她告訴我們原來在新聞標題裡出現了無數次的悲劇字眼,在真實發生時是這樣的體驗,這樣的含義。你彷彿可以透過她的懷抱,也觸摸到傷口。
有時候我忍不住想,為什麼環境可以這樣冷酷嚴寒,而人在其中又可以這樣堅強?
我想起她在書中所寫,莫斯科《新報》會議室牆上掛的6幅照片。
伊蓮娜寫,大家每天開編輯和選題會的會議室,掛著6幅黑白照片。不是什麼百年基業的前輩、捐款者,而是《新報》歷年遇害的調查報導記者。他們死於並不久遠的現在,2000至2009年。
「伊果、尤里、安娜、斯坦尼斯拉夫、安娜斯塔西雅、娜塔莉亞」,伊蓮娜寫下這6名記者遇害前正在做、或者已經發出的調查報導,以及他們遇害的具體情況。他們調查的是首長經濟腐敗、是執法者走私弊案、是軍方虐殺醜聞、是新納粹主義、是車臣暴政……他們被以不同的方式投毒暗殺、綁架殺害、當街槍擊。有些確認了兇手,卻無法確認主謀,有些則至今是懸案。
「每次有一張新的照片放上去,我們就試著把它與其他照片掛開一點,讓牆上不留多餘空間。」「當你無法保護自己和同伴時,自然會變得迷信起來。」伊蓮娜寫,「話雖如此,每次發生新的謀殺案,那些黑白肖像就會彼此靠得更近一些,而牆上總有空間再掛一張照片。」
我感到久久的震顫。我想像著黑白照片裡的人們不斷靠近的眼睛,看著曾跟他們一起日夜相處的同事們。我想像不到伊蓮娜看著他們時,感受到什麼。
還記得那個破壞了小伊蓮娜安逸人生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嗎?她先是成了她隔壁的同事,後來,她成了會議室牆上的黑白照片。安娜在2006年因為指控車臣共和國領導者虐待異己的調查報導,在自家公寓電梯內遭遇槍擊,6發子彈,2顆射中心臟,1顆在胸腔,1顆在頭部。
伊蓮娜寫,在安娜遇害後,「我花了好多個小時與死亡討價還價──如果馬上找到兇手,能不能讓她復活?如果我承諾把所有我想說卻不敢說的感謝話都告訴她,說她如何改變了我的生命和許許多多其他生命,她能不能死而復生?」
「她不能。」
文字有多少重量呢? 在捲入了更多生命的罪惡──在戰爭裡,《新報》這家成立了29年的媒體也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
它長期被認為是俄羅斯境內唯一具有影響力的敢言報紙。它的創始人、總編輯穆拉托夫曾在2021年,與菲律賓記者瑪麗亞.瑞薩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我記得穆拉托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我非常振奮,因為我認為現在他們可不敢殺他了。我非常振奮,因為世人(我們辦公室以外的所有人)終於有機會看見他的偉大。」伊蓮娜在結語裡這麼寫到。
而穆拉托夫在領獎時反覆提及,他知道這個獎並不是頒給自己,而是頒發給會議室牆上那6幅黑白照片,和許多與他們一樣的人們。
「他把獎金分給幾家慈善機構,自己一點也沒有留下。」伊蓮娜在書裡告訴我們。文字有多少重量呢?伊蓮娜在文章的最後問。
她已經流亡在俄羅斯以外,《新報》關閉,她和chosen family 失散了,但沒有一刻停下報導。
文字能對抗武裝暴政嗎?文字能阻擋戰爭嗎?文字能拯救一個國家嗎?文字能拯救把它說出來的人嗎?
伊蓮娜以一連串問題結尾。她給出了她的答案。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