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特权与压迫包装成“偏见”并不能合理化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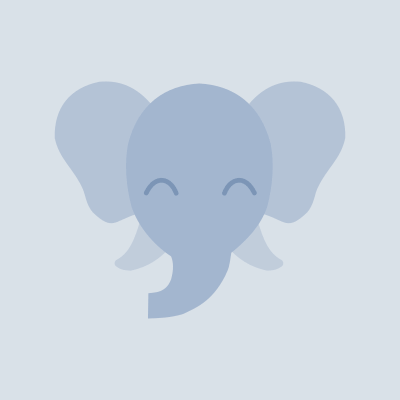
不得不承认许知远是个很懂得运用自身特权获取资源的人,否则也不会一季节目里能列出这一个怎么都说不上差的邀请名单,于是尽管我把许知远骂得狗血淋头,我还是得捏着鼻子吃下这口屎。不过既然吃了,那就至少得记录下每一期的大体,不让自己白白吃一顿。
第一期的罗振宇和许知远表面上似乎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维度的极端,但本质都是那个年代吃了时代和性别红利上位的人,是“中年异性恋男人”,他们最终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第二期的姚晨尽管聊了四个小时,但结果被剪进正片的不到二十分钟,正如许知远被制片人骂的“你的生活经验太局限了”,他和姚晨的访谈不过是毫无意义地试图将其人生线性地归纳出来,然而女性的记事与叙事方式却不是连续的,于是就会显得姚晨似乎什么都不记得,把整个访谈变得“似是而非”。 第三期的与二次元对话,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猎奇。如果批判动漫文化的浅薄与快餐化,那它充其量只是(后)福特主义时代下的一个折射,结果被许知远自以为是地局限在那一亩三分地,根本无法跳脱。 他始终只是试图用年代来划分某种特定类型的(男)人,企图将他所认为的二次元归纳到某种可以被解释为“精神匮乏”的,以此突出他自己所站的制高点。 第四期的冯小刚端着的那副架子,以至于有时候我都不能分辨出他偶尔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情感究竟是不是真心的。我始终不能理解他将《我不是潘金莲》说得那么“舍得一身剐”的动力是从哪来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正名他的成就吧。 第五期的叶准真的言之无物,许知远根本切不进命脉,作为北方人的他无法理解广府与香港在政治、地域、文化、语言上的异同,结果兜兜转转就只能围绕着那个年代的“出逃”来聊些浅显的玩意儿,更不用说他全程表现出的对咏春的不以为意。 第六期的李安真的很温柔,比起许知远这种“我懂得比你多,所以如果你做得不够‘对’,我就鄙视你的”知识分子,李安则是他知道他在时代洪流前的渺小,也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可是他知道他无法袖手旁观所以不得不做点什么。真的很可惜时间太短了,还没能更进一步就结束了。 第七期的张楚只能说他就是那个时代被推出来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被钉在那个位置上再也下不来了。你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吗?并没有。但他至少不试图重新掌握回这种主动权,这一点至少在许知远不断炮轰下都能四两拨千斤地打回去,比许知远高不知几个境界。 第八期的蔡澜印证了为什么我对他从小一直完全没有任何好感,因为他不过就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罢了。蔡澜聊十几岁时把比自己大几岁的女生搞大肚子,许知远居然问“后来怎么摆脱的”,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太羡慕你了”。 蔡澜解释他如何追求女性的时候说:“丑的照杀,好看的就会跟着来了,”许知远只是大笑然后敬酒“我太佩服你了”,最后连吃个鱼春都要问“这可以壮阳吗”,难怪他最后要说很久没有聊得这么尽兴了,毕竟真的臭味相投。 第九期的俞飞鸿是彻底地被撕下了他的假面具。当他和俞飞鸿聊武则天,结果认为武则天的行为是受制于女性身份的焦虑,还会反问她“你为什么对性别那么敏感”。 俞飞鸿的回答:“不得不承认这是男权社会”“认清事实本身”“本身构造就有区别”“我不会轻易喊女权”本身其实不完美,但是当她反问许知远“死亡是不是你们男人最大的恐惧”时,我觉得批评她不够激进是没意义的,能够打许知远脸即可。 “生命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活得有滋有味正是因为它的无意义。”或许她这句话正是解释了她无能反抗结构性的压迫的自我反省吧。 第十期的陈嘉映同样撕开了许知远的虚伪。一句“你真的不喜欢吗?”就击穿了他。“认识到虚伪不算难,认识虚伪下的真实才是最难的。” 同时也对许知远的“精英主义”很好地回应了:“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鼓吹什么就能改变思想观念,只能是因为社会结构变化。知识分子干的就是生产产品。 “过去想当然地把社会维持的高度“精英主义”认为是社会良性运转的代表,现在社会发展了自然就要遭到质疑。 “并不存在普遍的信念价值,世界上主要的价值变换都是随着西方的强势价值强加上来的。争取的不应该是论证它的普遍性,而是证明它被接受的原因:它的正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陈嘉映同样提到了“男权社会”,但是许知远却对此毫无反应。 第十一期的贾樟柯实在有些让人诧异,也许是拍摄时他正在经历他的人生一次转折,正如他说的他开始对人文性背后的不可琢磨产生了质疑,开始滑向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于是他的三个访谈都显得特别不一致。他在家乡的那段一对一的时长两个小时访谈里,能得到的信息几乎为零,他似乎根本不确定他正在面临的是什么。他在尝试的天体物理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结果很有可能是,什么都不是。 而第二段的所谓饭桌上男性的饭局则是一场漫长的折磨。饭桌上的中年异性恋男性的话语交换,永远围绕着政治之类的宏观结构,永远看不到“人”,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在推杯换盏中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网络。 唯一有价值的是他稍早一点的“单向街篇”。他谈到《三峡好人》时说到自己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流动的不可能性,导致他过往的乐观不复存在,甚至提出“只有另一个巨大的变革才能改变现在的变革”。他认为一直需要隐晦的社会文化是有问题的,缺乏的是坦率。但是这与他后续遁入对新技术的探讨和对超自然力的迷恋呈现出某种讽刺。 第十二期的金承志只能说是换了一个年代生存的顺直男遇到了所谓的“中年危机”。这一集非常清晰展现了许知远的采访能力为零的问题。他将这次访谈的浅薄归根于金承志的自我拒绝,倒不如说是他根本没办法想象除了他臆想出来的男性气质外更多的东西——异性恋时间、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对谁都要问“情欲对你重要吗”似乎离开了这种性上的掌控,他的男性气质就无法展露。 最后对青楼的探讨同样充满了顺直男对女性的凝视与物化,他们似乎在赞赏青楼女子的才华,但实际上不过是建立在这一“不光彩”的职业上对女性的性化。 第十三期和白先勇的时候,许知远聊到《孽子》时,估计又是怕尺度不对,又是被自身异性恋的特权蒙蔽,老是兜兜转转的,总在那些有些带有窥视的问题上打转,但是白先勇的回答又太过于充满那个年代特有的局限,最终只能得出个“一切为文学”“没什么不同”的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是“存在了这么久,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没有孔子教做人的道理就很难有中国历史的立足之地。 最后尾声时许知远归结出:“个人是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工具”无法讲清他究竟是过分的英雄主义还是擅长将人物化,或是两者都有,但始终能让人意识到他似乎从来未将“人”当“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