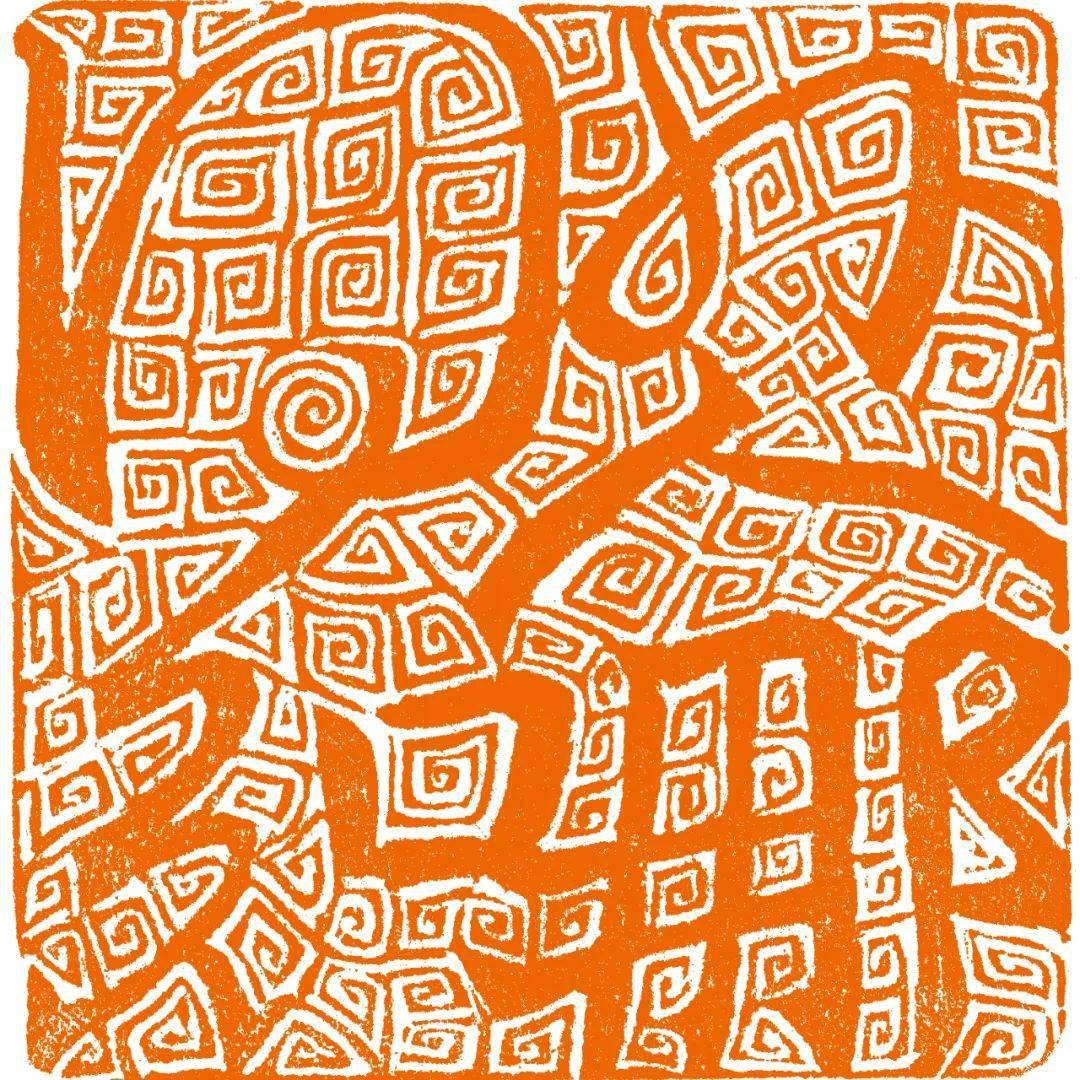翻译与校对:旧伤不改,新错频出
科马克·麦卡锡“边境三部曲”的中译本初版距今已十九年。十九年后,2021年3月,理想国出版了最新版。总结这个最新版,感受是八个字:旧伤不改,新错频出。旧伤指的是中译本对麦卡锡的本土化改写(乱改标点+东北、天津、北京、四川方言大乱炖),新错则指的是校对的疏忽和某些字词的改动。
之前已经简单总结过“边境三部曲”第一部《天下骏马》的翻译问题,详见拙文《本书翻译问题太多,可惜》。
《平原上的城市》中译本的特点是比较流畅,阅读上毫无难度,为了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友好”,甚至不惜更改麦卡锡的用词,比如,在男主人公约翰·格雷迪伤重将死之际,有这么段话:
他听见远处教堂悠远的钟声,听见自己低沉而急促的呼吸,意识到自己这当儿身处异地,躺在冰冷与黑暗里,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救救我,上帝,他心里呼唤着,阿门。
光读这段话,感觉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对比原文就会发现不对劲:
He heard the distant toll of bells from the cathedral in the city and he heard his own breath soft and uncertain in the cold and the dark of the child’s playhouse in that alien land where he lay in his blood. Help me, he said. If you think I’m worth it. Amen.
“soft and uncertain”被翻译成“低沉而急促”,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但的确是很诡异的误译。根据辞典的释义,soft除了最常见的“软、柔和的”的意思外,在这里可以理解成“轻柔、轻微到没有一丝力度”;“uncertain”除了最常见的“不确定的”的意思外,还可以理解成“不稳定的”,因此这里翻译成“微弱而不稳的呼吸”显然比“低沉而急促的呼吸”更符合原意,也谈不上有多难。译者这样翻译实在是太草率了。
漏译:上面这句话后面跟的那个“in the cold and the dark of the child’s playhouse”译者直接选择跳过不译。是不会译,不能译,还是觉得翻译了会“增加阅读理解的难度”,不得而知。
最后那句“Help me, he said. If you think I’m worth it. Amen.”(救救我,他说。如果你觉得我值得。阿门。)被译成“救救我,上帝,他心里呼唤着,阿门。”这句话没有任何难度,为什么这样翻译,莫名其妙,让人一头雾水。毫无道理。
或许同样是出于“照顾读者的阅读感受”而做出的改变是给麦卡锡的对话统统加上引号。麦卡锡小说中的对白一般不用引号(“一般”是因为我还没读完麦卡锡的所有作品,不敢妄下断言),无引号的好处是可以让对白相对自然地融入到叙述当中去——其实不管麦卡锡动机为何,艺术效果如何,翻译都应该尽量忠实原著——不把这点作为基础共识,那么对本书中译本的讨论就毫无意义。
如果说上述译法都能客观上起到“降低阅读难度,照顾读者感受”的目的的话,那么在对话中大量使用全国各地的方言这一操作的行为,就让我大惑不解了。我搞不明白,但大受震撼。直接附图举例吧:

龟儿子:川渝方言

到了儿:北京方言
(补一句,2002年初版作“到最后”,可能译者觉得味儿不够,后来的版本才改成了“到了儿”)

“你不仅是牛皮客(bullshitter),你还是大牛皮客!”——天水土话中把说话不着边际,爱吹牛,说大话,甚至以此行骗招摇的人叫“牛皮客”。

天津方言??
译者善用全国各地方言,但是对不熟悉方言的读者而言,可能会读得一头雾水。最搞笑的是,procurer(皮条客)被翻译成“龟头”,我是真的大受震撼,原来还有这种骂法?!

“那龟头用拳头打她……”
除了这些有点匪夷所思的译法外,把墨西哥人翻译成“老墨”我也想不通。我原以为原文用了某个口语化的表达,结果一查原文,用的是“they”!

they=老墨=墨西哥人
为了彻彻底底地汉化,译者简直是奇招迭出。虽然我觉得大可不必,但要说人家没有花心思,那也确实是睁眼瞎话。男主人公身上挨了四刀,原文说这四刀形成了个字母“E”。您猜怎么着,在中译本里,这个“E”成了“王”……

佩服得五体投地,译者确实太贴心了
前面提到,此书不仅旧伤不改,而且新错频出,“新错”指的是初版没有的错误,结果越印错误越多。刚开始阅读小说,第二页,就出现了一个低级错误,让我简直不得不怀疑自己买的是盗版书:

第二页,无句号
其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换乱的人称代词,在一句话中,“你”“您”混用。

人称代词混用
总的说来,这样的翻译质量和校对质量,都距离及格线有一定距离。这不免令人感到遗憾不已。